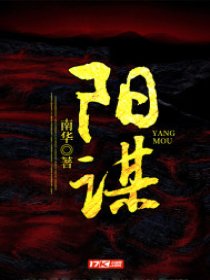第十四章:流年开花
黄欣悦躺在了洪美妮的家里,洪母正在给她熬鸡汤。
洪美妮索性关了店门,一直在陪着她。她将所有的一切都告诉了洪美妮,说自己不知道该有什么面目去见夏长风。
洪美妮却不以为然,她帮她梳理着头发,说:“你们只是喝多了,也不一定喝多了就是发生关系了,对吧?要不放心,去医院验验不就行了?”
洪母瞪了女儿一眼,说:“别给添乱了行不?让欣悦先把鸡汤喝了,静下来再思考以后的事。”
洪美妮撇撇嘴,继续又说:“你也太小题大做了吧?别说不一定有什么,就算是发生过什么,这个时代也是再正常不过的,如果你总是不能释怀,就嫁给他好了。”
黄欣悦窘迫得红了脸:“我是让你帮我理理头绪,你怎么回事?不仅不帮忙,还给拆台。”
“我说的是真话,顾明晨虽然脾气有点坏,但长得不错,又有钱,虽然有个孩子在身边,不过,也算不了什么大问题,要我说,他可是好对象呢!多少女孩子梦寐以求,打着灯笼都难找呢!”
黄欣悦听得更加糊涂了,不知道洪美妮什么意图:“你说什么呢?”
“我没有开玩笑,是在很认真地帮你分析,那是夏长风有千般万般的好,是你的青梅竹马,但是他在你的世界消失太久了,人是会变化的,也许他并不适合你了呢!你的精神本体表面和一只小仓鼠一样可爱、很宅,很安静,但其实你的灵魂本体却是一只不折不扣的刺猬,不会讨好,率真正直,时刻抵御着试图侵犯你的人,你重情感,不记仇,但是却真的非常怕受伤害,所以你迟疑不决……我倒是觉得,那个夏长风只是你的精神意象,顾明晨才是你贴心的生活伴侣……”
这番话居然把黄欣悦说得愣住了。
洪美妮还是语不惊人死不休:“听你这样一说,我总觉得顾明晨现在是非常在乎你的了,怕是已经欲罢不能了。你觉得你的心真的都在那个小时候的伙伴夏长风那里吗?不,不是的,你表面是拒绝了顾明晨,但是你的脚步却一点点向他靠近,你自己都意识不到……”
“什么?”黄欣悦居然哑口无言。
“看吧,还是我的占卜术灵吧?”洪美妮很得意地笑倒在沙发上。
洪母非常不满意女儿的所作所为,连忙制止了她:“赶紧喝汤,喝汤还堵不住你的嘴吗?欣悦已经够烦的了,让她静静。”
“是,母亲大人。”洪美妮笑着应了一声,乖乖坐下来,招呼着黄欣悦,“亲,快点吧!我母亲大人都烦我了。”
黄欣悦也不忍心老人家忙碌,也坐在洪美妮身边,舀了一口鸡汤。鸡汤的味道很鲜美,口感醇厚,越回味越有滋味,咽下去,还散发着淡淡的药香,这是添加黄芪、当归的味道,和表姨刘淑慧做的鸡汤味道很相似,但不知道为什么,有那么一丝不同。
她想着想着,鼻腔竟然酸了,她居然开始想念那个家了。这些年的生活,已经把她彻底融入到那个家庭里了,这种不同的味道,竟然就是那种思念的味道。她想,自己已经出来了好几天了,该回去看看了。
“对了,黄欣悦女士,你是不是嫌弃我送你的礼物不够好呀?上次我送你的生日礼物到现在你都没有领回,到底是几个意思呀?”
“没有什么意思,就是不能再收你的礼物了,我认识你这么久了,你送的礼物都堆成山了,这次就算是金矿,我也不收了。”
洪美妮看了一眼母亲担忧的眼神,偷偷示意她放心。她想了想,才说:“这是最后一次行吗?不要让我失望。”
黄欣悦很坚决地说:“你每次都这样说,这次我一定会坚持到底的,你就算给我送回家去,我也会原封不动地送回来,只要你家还在这个城市,我就一定会送回来的。”
洪美妮“哧”了一声,说:“都说是女人遇到男人,就会化成一朵莲花,温柔娴雅,但是你怎么经历的男人越多,就越倔得和石头一样,真想不通呀!”
黄欣悦终于知道所谓女人的语言是一把杀人于无形的刀,果然如此,这话说出来,她觉得刚才喝进去的鸡汤在胃里开始翻山倒海起来,于是,她起身冲进了卫生间里,开始呕吐起来。
外边飘进来一句洪美妮杀人不见血的话:“喂,你怎么回事?不会是真的怀孕了吧?算算日子,也不该呀!”
黄欣悦听了这话,顿时觉得胃里又一阵灼热翻涌过来,立刻又吐了起来。
“你这个孩子,怎么这么没谱呀?”洪母责怪洪美妮的声音再次传了过来。
“我这不是为了让她舒缓一下情绪嘛!谁料到她那小身子骨那么虚弱,真是虚不受补呀!”
黄欣悦折腾了好大一会儿,终于觉得自己的胃平复下来了。她看着镜子里的自己,头发散落,眼神涣散,似乎出窍的灵魂刚刚回转到躯体内,还不适应人间的生活,因此,她满脸都是沧桑与疲惫。
外面听起来虽然是洪母在训斥女儿,但是却不经意传递出发自母亲灵魂里的慈爱、关注与期待。这种感觉是黄欣悦最缺少的东西了。
她每次难过的时候,就想起姨父那岣嵝着身子裱画的影子。影子里流露出来的寂寞,是难以言表的。即便是他这一生沉默寡言,将自己全部投入到自己热爱的事业中,但是只要是人,都会有软肋,有伤心往事。姨父是个男人,但也是个有血有肉的男人,又何尝没有过遗憾与伤感呢?想起表姨的话里,她隐隐感觉到,姨父的记忆里,母亲颜雪珊一定是个重要的存在。
她觉着,到了该和姨父深深聊一聊的时候了。
顾明晨一直想把手机还给黄欣悦,但是他找不到她了。给她单利打过电话,刘淑慧说这几天都忙,没有回来。但是拍卖行没有人看到黄欣悦来过。顾明晨很懊悔,他为什么没有跟随在她后边,看她到底去了哪里。他当时以为她不愿意见他,所以便不敢再让她发现他的存在。他一度陷入了深深的自责中。
这一天,他被池宇航强行拉着到了一家意大利餐厅,池宇航说:“老顾,给你介绍个朋友,我的合作伙伴,我们打算采用一种新的形势来进军文化市场,是多元发展,不只是手工纸的保留与承扬。”
顾明晨知道池宇航做事素来没有章法,只是蹭了蹭鼻梁,笑了笑,但是,当他转身顺着池宇航至的方向望过去,才发现原来池宇航给自己介绍的这个人就是夏长风。
自从那次博览会上,他就记住了这个名字,记住了这个男人看黄欣悦的眼神,那种眼神是在惊喜与感动之外的一份浓浓情意。他非常不喜欢这个夏长风,甚至到了厌恶的地步。
夏长风初到北京,本想多结识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他也在别人口中听过这个作风雷厉风行的顾明晨的大名,所以,他很开心地站起来,看到的却是顾明晨黑着脸,不厌其烦的样子。
池宇航很奇怪顾明晨的异常,说起话来也有磕巴起来:“这是新家坡来的夏长风,他家原来也是老北京。这位是文道总经理顾明晨……”
话没有说完,顾明晨指着夏长风说:“我不会和这个人做朋友,商业上也没有更多合作的可能,对不起,我不奉陪了。”
他说完,转身走了几步,又回来,从上衣内侧兜里掏出一支女式手机,塞给夏长风说:“这件东西,拜托帮我还给她!还有,说一声抱歉,谢谢!以后我会向她解释。”
夏长风惊看手机片刻,看到自己给黄欣悦发的信息,终于明白了:“什么?这是她的手机?为什么会在你手里,怪不得我这些天联系不上她!”
“对不起,我没有和你解释的必要,再见,不,永远不要再见。”他说完,继续朝外走。
池宇航尴尬地朝着夏长风说:“稍等,夏先生,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等我沟通后再来。”
他一溜小跑,追着顾明晨喊着:“老顾,你这无名火发得莫名其妙呀?到底怎么回事?你们说的那个她是女的?是谁?”
顾明晨回头,瞪了一眼池宇航说:“她是谁不关你事,你去告诉那个夏长风,识相的话,赶紧回新家坡去!不要以一副假惺惺的面孔出现,去吧!”
“老顾,你这是无理取闹呀?什么时候也没见过你这么失水准呀?你知道不知道,外来的都是客,我们得尽地主之谊,就算是合作不成,也算交个朋友。这个社会,三个臭皮匠,一个诸葛亮,大家抱成一团,路才能走得远,不是吗?”池宇航也有些发怒,气得胸口都疼了。
但是,顾明晨却没有一点反转的余地,他指着池宇航的鼻子说:“你去和他做朋友好了,但是我要警告你,你有了他这个朋友,就不要再和我有任何交集了,听明白了没有?”
说完这句话,他迈开了坚定的步子,朝前走去。
池宇航气得弯着腰,大口大口呼了一口气,这才站直了气呼呼地说:“顾明晨呀,你早晚有一天得吃大亏,看吧!”
夏长风静静地坐在那里,远远看着两个人在争执,直到离去,不禁摇头淡淡一笑。他看到手机里的照片,都是修复古画的工作照片,竟然连一张自拍照片都没有。那里边有一张照片,很特别,稀疏的林子,微微翻绿,河开水暖,炊烟袅袅,说不出的灵动与典雅,下边写着几个字:“疏林寒绿图”。
他口中喃喃念着这几个字,很熟悉,似乎在哪里见过,但是,他真想不起,在哪里见过。那段记忆,失去的太久了,以致于那些散落在红尘的片段难以一一凝聚起来。
微信上除了自己的信息,就是这个顾明晨的公事公办的口气。他明白顾明晨的意思了,脸色开始收拢起来。
这家意大利餐厅的装潢很地道,墙壁上镶嵌着绘画、雕塑与各种各样的工艺品,洛可可式的水晶奢华大吊灯散发着华贵的温暖,三色对撞的窗帘非常夺人眼球,法式的优雅元素尽显其中。在看到顾明晨的那一刻,他感受到了对方那种凌厉的掠夺感。他起身离开了这里,去一个可以找到她的地方。
黄欣悦觉得自己应该回到表姨家里,再也不要去问道拍卖行了,也不要考虑顾明晨到底同意不同意自己辞职,只要自己不想,那任其是谁,又能拿自己怎么样呢?
她回家的步子走得很慢,从地铁口出来,几乎就是在慢行,这样慢慢行走才有更多的思考空间。四周是熟悉的道路,熟悉的店面,还有三三两两从胡同里出来的熟悉的人。她走着,忽然看到一群跑着玩耍的孩子后边,是一个熟悉的男人的背影。
他双手抄兜,站在第三株泡桐树下,阳光下影子修长。等孩子们远去了,他便后退几步,然后又朝前几步。那是一种徘徊的姿态,是一种停留等待的姿势,他在等什么人。
黄欣悦忽然捂着脸,泪水涌出。小时候遭受了太多的艰辛,她都不曾这样频繁哭过,但是近来却经常哭得尤其失控,有时甚至到了意识模糊的地步。于是,她不关别人的好奇张望,奔上去抱着他的腰,匍匐在他的后边大声哭了起来。
夏长风似乎“怔”了一下,然后迅速转身,将她紧紧抱住:“欣悦,吓死我了,我找不到你了,我还以为你出了什么事?”
黄欣悦哭了很久,才停止住,嗓音嘶哑起来:“我……我没事,就是去同学家住了两天。”
“好,没事就好,我就放心了。这样,我们去准备一下,去拜访表姨与姨父,求他们将你嫁给我。”
黄欣悦愣了:“你要和我结婚?”
夏长风重重点头,高兴地说:“欣悦,我很确定,永远不会变,你是我唯一的爱人。你看,这是什么?”
黄欣悦惊讶地看到夏长风拿出了一只熠熠生辉的钻戒,她忽然退后了几步。
夏长风愣了,他以为她会高兴地让他把戒指戴在手上。
“怎么?”
黄欣悦摇头:“不,长风,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觉得,你不需要征得母亲的同意吗?现在虽然婚姻自由了,但是没有长辈的祝福,婚姻很难得到真正的幸福。”
“只要我们在一起就好了,我们彼此错过了太多的日子了,我不想再放你走了。结婚后,我们夫唱妇随,把北京这家分公司打理好,我们可以把中国一流的纸品都采办过来,在北京住一段时间,就去新加坡住一段时间,总之,你要你愿意,我都随你,不好吗?”
黄欣悦看了看夏长风,忽然问道:“我还想和姨父再学习一下裱画,虽然我现在的技艺精进了很多,但是遇到棘手的问题还是解决不了,所以,我想再晚点再考虑结婚的事。”
“难道,你不愿意早一些和我在一起吗?”夏长风有些焦急,猜不透黄欣悦心里想些什么。
“长风,我很想和你在一起,但是裱画需要摒弃人间一切私欲杂念,所以一定要感受寂寞,我们虽然可以在商海一同拼杀,但是最后却永远达不成我的这个心愿了。”
夏长风摆手不解:“我不明白,这有什么矛盾?”
“有的。小时候我不懂,为什么姨父放弃了在学校里的大好前途,甘愿做一个默默无闻的裱画师呢?现在我懂了,这便是得失,得到的时候也意味着失去……我父亲把造纸术记录下来,其实就是想将它发扬光大,可惜他没有实现自己的心愿,所以我把这技艺传给小磊,云青还有更多的父老乡亲,就是因为凭我个人之力,难以达成这个愿望。我只有一双手,两条腿,一个身躯,生命又非永恒,唯一可做的就是抓住稍纵即逝的时光,做让自己灵魂饱满的事。现在,我还是要静下心来,去学习姨父的裱画技艺。”
夏长风很吃惊,他摆着手,依旧说:“我还是不明白……”
黄欣悦觉得自己头很乱,她后退了几步,说:“对不起,我要先回去了,我有些累了……”
她转身开始朝胡同里走去,不知道为什么,她很想静一静。
“等等。”夏长风追了过来,朝她手里塞了一件东西。
黄欣悦看到那居然是自己的手机,于是惊讶问道:“怎么会在你那里?”
夏长风的口气很淡:“是顾明晨让我转交给你的,他说怕你不理他。”
黄欣悦点头:“原来他去找你了。”
夏长风苦笑:“他对我很不友好,把我的商业计划都给摧毁了。”
黄欣悦听了这话,心头莫名其妙跳了一下,她说:“对不起,改天我们再谈,今天真的要走了。”
夏长风看着自己手里的戒指,呆了片刻,只好点头,就这样看她消失了胡同深处。他还没有勇气追过去,从小就没有勇气踏进那个胡同。
他想起来了,他九岁那年曾经想找过她,只是在胡同里打听她家的具体门牌,但是当他提到“黄欣悦”的名字的时候,就看到胡同里出来了一个,穿着花筒裤、提着菜篮子的阿姨,那女人身材很壮,神态晦暗,瞪着眼睛朝自己骂着:“谁家的小兔崽子,来找我家欣悦干什么?告诉你,她还是个好端端的清白姑娘,容不得你们这些小脏鬼们想入非非的,赶紧滚,滚得越远越好……”
小小年纪的他窘迫得红了脸,他只退后几步,还是不甘心离开,只见那女人四处寻着,终于在一家木门前边的一小块花圃的竹竿栅栏上抽了一根出来,作势吓唬着:“怎么?还不走?再不走我可就打断你的腿,不信,你试试!”
胳膊拧不过大腿,他只好黯然离开。他从来没有见过这么丑陋这么凶悍的女人,他替小欣悦有些委屈,她生活在这样一个粗俗的女人手里,难道还有什么好日子过吗?他开始心疼她,发誓以后都要好好保护这个善良的小姑娘。
他还是不太明白,明明两个人志同道合,明明就可以成为彼此依靠的人,为什么她会拒绝他的求婚?他想了片刻,还是决定要把北京的分公司做大做强,这样才可以光明正大地来她家求婚。于是,他转身,离开这里。
黄欣悦走着,莫名觉得心中忐忑不安,她说不好是为了什么,也搞不清楚自己的心为什么如此慌乱?她的心宁静不下来,也无法凝神接受夏长风。
她越朝里边走,就越觉得不对劲,表姨家的门口站满了人,大家唉声叹气,纷纷议论着什么。院子里似乎听到表姨歇斯底里的哭泣声:“我的儿啊,你这是要了你妈的命呀!”
她蓦地觉察出又什么不对,胡同口刚才停了不少车,她本来还奇怪是谁家来了亲戚,原来竟然都是朝着表姨家来的。她急切地推开众人,挤了进去。果然,表姨刘淑惠坐在地上哭天抢地,任婷居然也在家里。
任婷一边扶着母亲,一边也抹着眼泪,看到黄欣悦的时候,居然愤怒起来,上前就扬手掴了她一掌:“黄欣悦,你还知道回来呀?这个家白养你了,出了这么大的事,都找不到你的人影,你到底干什么去了?”
黄欣悦捂着脸,不解地问:“出了什么事?”
只见任婷忽然抽泣起来:“鹏鹏死了……被人捅了一刀,连肠子都流出来,死了两天了,被丢在郊区的一所鱼塘里,如果不是正巧有人去钓鱼,还不知道……”
“啊?”黄欣悦觉得心脏蓦地抽紧了起来,她不可置信地退了几步,摇头:“不可能……这怎么可能……发生了什么事?”
“就是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现在警察叫喊爸过去做笔录去了,现在暂时还不让我们见人,说是勘验完再让我们见面。”
黄欣悦软绵绵地走过去,想扶住表姨刘淑惠,不料表姨却挣脱了她的手,恨恨地说:“他到底不是你的亲弟弟,你才这么懈怠,我早就让你们姐妹两个多帮帮他,给他找个像样的工作,现在可好了,四处被人追债,还死于非命……让我这白发人送给黑发人,这可让我怎么活呀?”说完,又抽噎起来。
听到表姨将这一切责任推诿在自己这里,黄欣悦不知道该如何自辩。
“不要以为我是瞎子,告诉你,我可是过来人。你和那个顾明晨不清不白,还和一个长得英俊潇洒的年轻人在胡同里暧昧不清……我是亲眼看见了……我以为我会把你带好,没想到是功亏一篑,你到底是承继你的亲娘那狐媚子的妖性……我真是后悔,真不该留着你……”
黄欣悦惊呆了,看到任婷咬牙切齿瞪着自己说:“我早就告诉过你,顾明晨是我看上的男人,你不许和我抢……没想到,你还变本加厉了。妈都告诉我了,顾明晨不仅不许你辞职,还给你升职加薪了……你告诉我,你到底用了什么手腕,才让顾明晨对你死心塌地?”
“我没有……”黄欣悦委屈地咬着唇,很想告诉她们,自己已经有爱人了,不是顾明晨,但是她看到门外都是看热闹的人,不知道说了会不会有人相信,怕是流言更加漫天飞了。
“事实证据确凿,今天早上公司例会,已经宣布了你的事,难道你想否认?”
黄欣悦正想再解释自己一定不会再去公司任职的,忽然看到门外安静了下来,只见任婷的同学李鸿陪着姨父一前一后走进来。
不过几天没见,姨父的白发又增加了许多,他走得很慢,并没有说一句,只是一个人默默地走到院子里的太师椅上,无力地坐了下来。他那衰老的容颜与涣散的眼神,掩饰不知那发自内心的蚀骨的悲恸。
此刻,刘淑惠似乎凝聚了全身的气力,几步冲了过去,拉扯着丈夫的手,问:“怎么样?见到了吗?”
任文良点点头:“只是远远看了一眼,说是明天我们就可以去办手续领取尸体了。”
刘淑惠哀哀地看了一眼天空,顿时跌坐在地上,又嚎啕大哭起来。任婷也随着母亲啜泣起来,李鸿赶紧过来扶住任婷。几个街坊邻居都跑进来,将刘淑惠扶起,安置坐下,你一句我一句纷纷安慰劝说她要节哀顺变。黄欣悦也很担心表姨,但是不敢上前,只好一个人站在院子里人少的地方。
任文良长长叹息了一口气,哀声说:“谢谢他这些大伯大妈们怜悯,这孩子自小就不争气,现在是自作孽、不可活,我们这作父母的,也是尽了力了,既然是命,我们也就认了吧!”
邻居们又开始嗟叹和安慰。
忽然,刘淑惠的身子颤抖了几下,似乎被注入了一股邪恶的能量,她指着黄欣悦对任文良说:“你还好意思说,今天当着大家的面,我也不怕家丑外扬了,任文良,告诉你,都是你把我给逼的,你逼死了你儿子,不如现在也把我的命拿去,我受够了!”
任文良皱着眉头怒说:“都是你把他惯的,只知道宠溺,不教他做人,现在都是自食恶果,现在还怪谁呢?我们的都有错,现在也遭到惩罚了。”
刘淑惠凄厉地仰天大笑几声,又开始痛哭流涕地说:“这孩子虽然有些不太稳妥,但是并不是个不可救药的。如果你对他稍稍加些关心,和对待那个女人的女儿一样多花些心思教导他,他怎么会遭遇到难处都不敢回家,最后把自己给逼死了!你居然还说,都是他的错!任文良,我恨你,恨你一辈子都没有把心放在我和自己的亲生骨肉身上!”
“你胡说什么?”任文良听到妻子这样说,脸色涨红得和紫茄一般,颤颤巍巍地站起身来。
“我是什么你心里明白!”刘淑惠仿佛忽然醒悟了,一口气将积压在自己心头多年的恶气一并发泄出来,她指着黄欣悦冷笑,“实话对你说,我一看到她就想起那个女人,想起那个你得不到的女人。我从嫁给你之前,就知道你这辈子最厌恶剽窃别人的劳动成果,你曾经险些与你的师傅对抗,不学那临摹术,但是你最后却由于那个人改变了初衷。你这一辈子就只临摹了那一幅画,你废寝忘食,穷其所能,就是为了那个女人,你现在还不敢承认吗?你知道吗?我每次在你屋子里收拾出那些废纸的草稿纸,我都恨不得将它们都吃下去!”
任婷看到母亲如此哀绝,也忽然对自己的父亲说:“爸,我和妈一样,不喜欢那个女人和她的孩子,这也是我不愿意回家的原因。我小时候常常看到母亲人前强颜欢笑,背后悄悄抹眼泪,我就知道她这辈子,定然是受了极大的委屈!爸,是你,伤了我妈的心!”
她说着,忽然狠狠瞪起眼,朝着黄欣悦冲了过去,狠狠撕扯着她的头发,歇斯底里地拳打脚踢,边哭边骂起来:“如果不是因为你母亲和你的出现,我们这个家就会过的好好的,我妈她不会这么伤心,我弟弟也不会死!我恨死你了!”
黄欣悦没有躲避,她忍着肌肤上传来的撕心裂肺的疼痛,忍着被人撕扯的难堪,默默无语。她也记得表姨经常偷偷抹着眼泪,却不知道为什么,也许正因为她们所说,是自己的母亲和自己造的孽。如果真的躲不开这孽债,如果这样可以让表姨失去亲生骨肉的痛苦减轻一些,她愿意承受。
但是,她还没有来的及再思考下去,忽然听到任婷喊了一声:“爸!”
只见任文良冷着脸,重重地给了任婷一巴掌。这巴掌传递过来的声音在杂乱的人声中尤为清晰响亮,众人顿时都懵了。
任婷被父亲可怕的面孔惊吓住了,她捂着脸,两眼含泪,一步一步朝后退去。李鸿急忙冲上前,一把搂起她,将她迅速拉扯到角落里,柔声安慰起来。
任文良的表情非常凝重,他推开众人的阻拦,转身朝刘淑惠走过去,郑重地说:“淑惠,我知道你对我怨气很重,但是我没有对不起你,也没有对不起这个家,任鹏他有他的命数,我们只能教他走路,不能永远搀扶着他走路。他小时候,我让他去买白矾,他去看人家逗蝈蝈,白矾洒了一半还多。我让他学裱画,他嫌累,兑现慢。让他去学英语,结果他半途又废了跑去赌钱。我昧着良心,将那临摹画给了他,不就是为了救他?可是,他能体会到父母的苦心吗?”
刘淑惠被他的表情也震慑住了,忽然,她浑身抽动了几下,闭着眼便朝后倒了下去。这个紧急情况,把大家又给吓了一跳,立刻有人上去掐人中,有人上去搓手。邻居周大爷家的小儿子正在中医药大学读研究生,见到这情形,连忙上前在刘淑惠的人中、百会、合谷等穴位扎了上去,过了不久,只见刘淑惠才悠悠转醒。她嘴角抽动了两下,呼吸渐渐均匀,眼角又渗出几滴眼泪,但是还是不肯睁开眼睛。
任婷此刻也哭得几乎上不来气,躲在李鸿的胸前哽咽着。
黄欣悦看到任文良仍旧走过来对她说:“欣悦,你暂且先回避一下,她们母女两个是太伤心了,没有地方发泄,让你受委屈了,你先回你的公司去工作,等过些日子,她们的情绪渐渐回复过来再回家来,好好和她们聊一聊。”
这几句说完,黄欣悦终于抑制不住自己的眼泪流了下来。一个刚刚遭受了丧子之痛的父亲,一个洁身自好、素来注重好声名的男人,刚刚在众目睽睽之下,被妻子和女儿指责,那种渗入灵魂的悲恸该有多深,但是此刻,他还是顾念着自己的感受,这些关爱,让黄欣悦感受无地自容,感到难以承受这份恩情。
“姨父,我可以多知道些我父母和您的故事吗?”黄欣悦知道此刻并不适合说这些话,但此刻又是打开姨父心扉的最好时机,所以,她鼓起勇气问了出来。
任文良的眼神里流泄出一丝异样的光,慢慢点头:“好,我答应你,等办完了任鹏的丧事,我就好好说给你听。”
“您多保重……姨以为多保重……”
黄欣悦抹了一把眼泪,看到四处都是摇头叹气的目光,无奈,只好一步一步慢慢朝外走去。她真的不想离开,她只想在这个家最困难的时刻,和自己最在乎的家人,一起渡过,欢乐也好,悲伤也好,只要可以和家人在一起,什么样的苦她都可以承受。可是,现在的她,居然成了这个家最憎恶的人。
她想不开,这究竟是为了什么?母亲,如果你还在这个人世,可不可以回来,告诉你的女儿,这究竟是怎么样一段宿怨?过去的时光里藏着怎样凄婉难堪的往事?她的脑海里不停浮现出过去的点点滴滴,那间曾经遭遇过大火的中药店,就是夏长风的家,似乎也隐藏了什么难以洞悉的往事?她想得头疼欲裂,不知不觉快要走到胡同口的大街上。
“黄女士,又有您的快递。”她看到上次给自己送生日蛋糕的快递小哥正朝自己笑着,“上次的蛋糕比较重,这次就轻飘飘的,好像是一份文件。”
黄欣悦勉强控制住自己的情绪,对快递小哥说了声:“谢谢。”
她的手有些微微颤抖,但还是打开了那文件,她万万没有想到,那居然是一张法院的传票。原告就是上次到自己家裱画,被自己剔除掉纸张里的头发丝的男人,叫邓玉春,他告自己以裱画为名,用不正当手段换了他家的原画,他要求黄欣悦将他家的原画完整奉还,还要赔偿他因此次造成的经济损失与精神损失费五百万。
她觉得自己的视线有些模糊,前边似乎来来往往很多车辆,还有一个男人忽然出现,挡住了自己。她不知道,自己就这样朝地上倒去,只是残留的意识里,仿佛有人轻轻揽住了自己的腰身,轻轻叹息了一声。那声音有些熟悉,也有些惋惜与心疼的意味。
四周的树木与建筑物旋转起来,天地一片昏黑,她似乎渐渐进入了一个未知的世界。
洪美妮索性关了店门,一直在陪着她。她将所有的一切都告诉了洪美妮,说自己不知道该有什么面目去见夏长风。
洪美妮却不以为然,她帮她梳理着头发,说:“你们只是喝多了,也不一定喝多了就是发生关系了,对吧?要不放心,去医院验验不就行了?”
洪母瞪了女儿一眼,说:“别给添乱了行不?让欣悦先把鸡汤喝了,静下来再思考以后的事。”
洪美妮撇撇嘴,继续又说:“你也太小题大做了吧?别说不一定有什么,就算是发生过什么,这个时代也是再正常不过的,如果你总是不能释怀,就嫁给他好了。”
黄欣悦窘迫得红了脸:“我是让你帮我理理头绪,你怎么回事?不仅不帮忙,还给拆台。”
“我说的是真话,顾明晨虽然脾气有点坏,但长得不错,又有钱,虽然有个孩子在身边,不过,也算不了什么大问题,要我说,他可是好对象呢!多少女孩子梦寐以求,打着灯笼都难找呢!”
黄欣悦听得更加糊涂了,不知道洪美妮什么意图:“你说什么呢?”
“我没有开玩笑,是在很认真地帮你分析,那是夏长风有千般万般的好,是你的青梅竹马,但是他在你的世界消失太久了,人是会变化的,也许他并不适合你了呢!你的精神本体表面和一只小仓鼠一样可爱、很宅,很安静,但其实你的灵魂本体却是一只不折不扣的刺猬,不会讨好,率真正直,时刻抵御着试图侵犯你的人,你重情感,不记仇,但是却真的非常怕受伤害,所以你迟疑不决……我倒是觉得,那个夏长风只是你的精神意象,顾明晨才是你贴心的生活伴侣……”
这番话居然把黄欣悦说得愣住了。
洪美妮还是语不惊人死不休:“听你这样一说,我总觉得顾明晨现在是非常在乎你的了,怕是已经欲罢不能了。你觉得你的心真的都在那个小时候的伙伴夏长风那里吗?不,不是的,你表面是拒绝了顾明晨,但是你的脚步却一点点向他靠近,你自己都意识不到……”
“什么?”黄欣悦居然哑口无言。
“看吧,还是我的占卜术灵吧?”洪美妮很得意地笑倒在沙发上。
洪母非常不满意女儿的所作所为,连忙制止了她:“赶紧喝汤,喝汤还堵不住你的嘴吗?欣悦已经够烦的了,让她静静。”
“是,母亲大人。”洪美妮笑着应了一声,乖乖坐下来,招呼着黄欣悦,“亲,快点吧!我母亲大人都烦我了。”
黄欣悦也不忍心老人家忙碌,也坐在洪美妮身边,舀了一口鸡汤。鸡汤的味道很鲜美,口感醇厚,越回味越有滋味,咽下去,还散发着淡淡的药香,这是添加黄芪、当归的味道,和表姨刘淑慧做的鸡汤味道很相似,但不知道为什么,有那么一丝不同。
她想着想着,鼻腔竟然酸了,她居然开始想念那个家了。这些年的生活,已经把她彻底融入到那个家庭里了,这种不同的味道,竟然就是那种思念的味道。她想,自己已经出来了好几天了,该回去看看了。
“对了,黄欣悦女士,你是不是嫌弃我送你的礼物不够好呀?上次我送你的生日礼物到现在你都没有领回,到底是几个意思呀?”
“没有什么意思,就是不能再收你的礼物了,我认识你这么久了,你送的礼物都堆成山了,这次就算是金矿,我也不收了。”
洪美妮看了一眼母亲担忧的眼神,偷偷示意她放心。她想了想,才说:“这是最后一次行吗?不要让我失望。”
黄欣悦很坚决地说:“你每次都这样说,这次我一定会坚持到底的,你就算给我送回家去,我也会原封不动地送回来,只要你家还在这个城市,我就一定会送回来的。”
洪美妮“哧”了一声,说:“都说是女人遇到男人,就会化成一朵莲花,温柔娴雅,但是你怎么经历的男人越多,就越倔得和石头一样,真想不通呀!”
黄欣悦终于知道所谓女人的语言是一把杀人于无形的刀,果然如此,这话说出来,她觉得刚才喝进去的鸡汤在胃里开始翻山倒海起来,于是,她起身冲进了卫生间里,开始呕吐起来。
外边飘进来一句洪美妮杀人不见血的话:“喂,你怎么回事?不会是真的怀孕了吧?算算日子,也不该呀!”
黄欣悦听了这话,顿时觉得胃里又一阵灼热翻涌过来,立刻又吐了起来。
“你这个孩子,怎么这么没谱呀?”洪母责怪洪美妮的声音再次传了过来。
“我这不是为了让她舒缓一下情绪嘛!谁料到她那小身子骨那么虚弱,真是虚不受补呀!”
黄欣悦折腾了好大一会儿,终于觉得自己的胃平复下来了。她看着镜子里的自己,头发散落,眼神涣散,似乎出窍的灵魂刚刚回转到躯体内,还不适应人间的生活,因此,她满脸都是沧桑与疲惫。
外面听起来虽然是洪母在训斥女儿,但是却不经意传递出发自母亲灵魂里的慈爱、关注与期待。这种感觉是黄欣悦最缺少的东西了。
她每次难过的时候,就想起姨父那岣嵝着身子裱画的影子。影子里流露出来的寂寞,是难以言表的。即便是他这一生沉默寡言,将自己全部投入到自己热爱的事业中,但是只要是人,都会有软肋,有伤心往事。姨父是个男人,但也是个有血有肉的男人,又何尝没有过遗憾与伤感呢?想起表姨的话里,她隐隐感觉到,姨父的记忆里,母亲颜雪珊一定是个重要的存在。
她觉着,到了该和姨父深深聊一聊的时候了。
顾明晨一直想把手机还给黄欣悦,但是他找不到她了。给她单利打过电话,刘淑慧说这几天都忙,没有回来。但是拍卖行没有人看到黄欣悦来过。顾明晨很懊悔,他为什么没有跟随在她后边,看她到底去了哪里。他当时以为她不愿意见他,所以便不敢再让她发现他的存在。他一度陷入了深深的自责中。
这一天,他被池宇航强行拉着到了一家意大利餐厅,池宇航说:“老顾,给你介绍个朋友,我的合作伙伴,我们打算采用一种新的形势来进军文化市场,是多元发展,不只是手工纸的保留与承扬。”
顾明晨知道池宇航做事素来没有章法,只是蹭了蹭鼻梁,笑了笑,但是,当他转身顺着池宇航至的方向望过去,才发现原来池宇航给自己介绍的这个人就是夏长风。
自从那次博览会上,他就记住了这个名字,记住了这个男人看黄欣悦的眼神,那种眼神是在惊喜与感动之外的一份浓浓情意。他非常不喜欢这个夏长风,甚至到了厌恶的地步。
夏长风初到北京,本想多结识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他也在别人口中听过这个作风雷厉风行的顾明晨的大名,所以,他很开心地站起来,看到的却是顾明晨黑着脸,不厌其烦的样子。
池宇航很奇怪顾明晨的异常,说起话来也有磕巴起来:“这是新家坡来的夏长风,他家原来也是老北京。这位是文道总经理顾明晨……”
话没有说完,顾明晨指着夏长风说:“我不会和这个人做朋友,商业上也没有更多合作的可能,对不起,我不奉陪了。”
他说完,转身走了几步,又回来,从上衣内侧兜里掏出一支女式手机,塞给夏长风说:“这件东西,拜托帮我还给她!还有,说一声抱歉,谢谢!以后我会向她解释。”
夏长风惊看手机片刻,看到自己给黄欣悦发的信息,终于明白了:“什么?这是她的手机?为什么会在你手里,怪不得我这些天联系不上她!”
“对不起,我没有和你解释的必要,再见,不,永远不要再见。”他说完,继续朝外走。
池宇航尴尬地朝着夏长风说:“稍等,夏先生,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等我沟通后再来。”
他一溜小跑,追着顾明晨喊着:“老顾,你这无名火发得莫名其妙呀?到底怎么回事?你们说的那个她是女的?是谁?”
顾明晨回头,瞪了一眼池宇航说:“她是谁不关你事,你去告诉那个夏长风,识相的话,赶紧回新家坡去!不要以一副假惺惺的面孔出现,去吧!”
“老顾,你这是无理取闹呀?什么时候也没见过你这么失水准呀?你知道不知道,外来的都是客,我们得尽地主之谊,就算是合作不成,也算交个朋友。这个社会,三个臭皮匠,一个诸葛亮,大家抱成一团,路才能走得远,不是吗?”池宇航也有些发怒,气得胸口都疼了。
但是,顾明晨却没有一点反转的余地,他指着池宇航的鼻子说:“你去和他做朋友好了,但是我要警告你,你有了他这个朋友,就不要再和我有任何交集了,听明白了没有?”
说完这句话,他迈开了坚定的步子,朝前走去。
池宇航气得弯着腰,大口大口呼了一口气,这才站直了气呼呼地说:“顾明晨呀,你早晚有一天得吃大亏,看吧!”
夏长风静静地坐在那里,远远看着两个人在争执,直到离去,不禁摇头淡淡一笑。他看到手机里的照片,都是修复古画的工作照片,竟然连一张自拍照片都没有。那里边有一张照片,很特别,稀疏的林子,微微翻绿,河开水暖,炊烟袅袅,说不出的灵动与典雅,下边写着几个字:“疏林寒绿图”。
他口中喃喃念着这几个字,很熟悉,似乎在哪里见过,但是,他真想不起,在哪里见过。那段记忆,失去的太久了,以致于那些散落在红尘的片段难以一一凝聚起来。
微信上除了自己的信息,就是这个顾明晨的公事公办的口气。他明白顾明晨的意思了,脸色开始收拢起来。
这家意大利餐厅的装潢很地道,墙壁上镶嵌着绘画、雕塑与各种各样的工艺品,洛可可式的水晶奢华大吊灯散发着华贵的温暖,三色对撞的窗帘非常夺人眼球,法式的优雅元素尽显其中。在看到顾明晨的那一刻,他感受到了对方那种凌厉的掠夺感。他起身离开了这里,去一个可以找到她的地方。
黄欣悦觉得自己应该回到表姨家里,再也不要去问道拍卖行了,也不要考虑顾明晨到底同意不同意自己辞职,只要自己不想,那任其是谁,又能拿自己怎么样呢?
她回家的步子走得很慢,从地铁口出来,几乎就是在慢行,这样慢慢行走才有更多的思考空间。四周是熟悉的道路,熟悉的店面,还有三三两两从胡同里出来的熟悉的人。她走着,忽然看到一群跑着玩耍的孩子后边,是一个熟悉的男人的背影。
他双手抄兜,站在第三株泡桐树下,阳光下影子修长。等孩子们远去了,他便后退几步,然后又朝前几步。那是一种徘徊的姿态,是一种停留等待的姿势,他在等什么人。
黄欣悦忽然捂着脸,泪水涌出。小时候遭受了太多的艰辛,她都不曾这样频繁哭过,但是近来却经常哭得尤其失控,有时甚至到了意识模糊的地步。于是,她不关别人的好奇张望,奔上去抱着他的腰,匍匐在他的后边大声哭了起来。
夏长风似乎“怔”了一下,然后迅速转身,将她紧紧抱住:“欣悦,吓死我了,我找不到你了,我还以为你出了什么事?”
黄欣悦哭了很久,才停止住,嗓音嘶哑起来:“我……我没事,就是去同学家住了两天。”
“好,没事就好,我就放心了。这样,我们去准备一下,去拜访表姨与姨父,求他们将你嫁给我。”
黄欣悦愣了:“你要和我结婚?”
夏长风重重点头,高兴地说:“欣悦,我很确定,永远不会变,你是我唯一的爱人。你看,这是什么?”
黄欣悦惊讶地看到夏长风拿出了一只熠熠生辉的钻戒,她忽然退后了几步。
夏长风愣了,他以为她会高兴地让他把戒指戴在手上。
“怎么?”
黄欣悦摇头:“不,长风,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觉得,你不需要征得母亲的同意吗?现在虽然婚姻自由了,但是没有长辈的祝福,婚姻很难得到真正的幸福。”
“只要我们在一起就好了,我们彼此错过了太多的日子了,我不想再放你走了。结婚后,我们夫唱妇随,把北京这家分公司打理好,我们可以把中国一流的纸品都采办过来,在北京住一段时间,就去新加坡住一段时间,总之,你要你愿意,我都随你,不好吗?”
黄欣悦看了看夏长风,忽然问道:“我还想和姨父再学习一下裱画,虽然我现在的技艺精进了很多,但是遇到棘手的问题还是解决不了,所以,我想再晚点再考虑结婚的事。”
“难道,你不愿意早一些和我在一起吗?”夏长风有些焦急,猜不透黄欣悦心里想些什么。
“长风,我很想和你在一起,但是裱画需要摒弃人间一切私欲杂念,所以一定要感受寂寞,我们虽然可以在商海一同拼杀,但是最后却永远达不成我的这个心愿了。”
夏长风摆手不解:“我不明白,这有什么矛盾?”
“有的。小时候我不懂,为什么姨父放弃了在学校里的大好前途,甘愿做一个默默无闻的裱画师呢?现在我懂了,这便是得失,得到的时候也意味着失去……我父亲把造纸术记录下来,其实就是想将它发扬光大,可惜他没有实现自己的心愿,所以我把这技艺传给小磊,云青还有更多的父老乡亲,就是因为凭我个人之力,难以达成这个愿望。我只有一双手,两条腿,一个身躯,生命又非永恒,唯一可做的就是抓住稍纵即逝的时光,做让自己灵魂饱满的事。现在,我还是要静下心来,去学习姨父的裱画技艺。”
夏长风很吃惊,他摆着手,依旧说:“我还是不明白……”
黄欣悦觉得自己头很乱,她后退了几步,说:“对不起,我要先回去了,我有些累了……”
她转身开始朝胡同里走去,不知道为什么,她很想静一静。
“等等。”夏长风追了过来,朝她手里塞了一件东西。
黄欣悦看到那居然是自己的手机,于是惊讶问道:“怎么会在你那里?”
夏长风的口气很淡:“是顾明晨让我转交给你的,他说怕你不理他。”
黄欣悦点头:“原来他去找你了。”
夏长风苦笑:“他对我很不友好,把我的商业计划都给摧毁了。”
黄欣悦听了这话,心头莫名其妙跳了一下,她说:“对不起,改天我们再谈,今天真的要走了。”
夏长风看着自己手里的戒指,呆了片刻,只好点头,就这样看她消失了胡同深处。他还没有勇气追过去,从小就没有勇气踏进那个胡同。
他想起来了,他九岁那年曾经想找过她,只是在胡同里打听她家的具体门牌,但是当他提到“黄欣悦”的名字的时候,就看到胡同里出来了一个,穿着花筒裤、提着菜篮子的阿姨,那女人身材很壮,神态晦暗,瞪着眼睛朝自己骂着:“谁家的小兔崽子,来找我家欣悦干什么?告诉你,她还是个好端端的清白姑娘,容不得你们这些小脏鬼们想入非非的,赶紧滚,滚得越远越好……”
小小年纪的他窘迫得红了脸,他只退后几步,还是不甘心离开,只见那女人四处寻着,终于在一家木门前边的一小块花圃的竹竿栅栏上抽了一根出来,作势吓唬着:“怎么?还不走?再不走我可就打断你的腿,不信,你试试!”
胳膊拧不过大腿,他只好黯然离开。他从来没有见过这么丑陋这么凶悍的女人,他替小欣悦有些委屈,她生活在这样一个粗俗的女人手里,难道还有什么好日子过吗?他开始心疼她,发誓以后都要好好保护这个善良的小姑娘。
他还是不太明白,明明两个人志同道合,明明就可以成为彼此依靠的人,为什么她会拒绝他的求婚?他想了片刻,还是决定要把北京的分公司做大做强,这样才可以光明正大地来她家求婚。于是,他转身,离开这里。
黄欣悦走着,莫名觉得心中忐忑不安,她说不好是为了什么,也搞不清楚自己的心为什么如此慌乱?她的心宁静不下来,也无法凝神接受夏长风。
她越朝里边走,就越觉得不对劲,表姨家的门口站满了人,大家唉声叹气,纷纷议论着什么。院子里似乎听到表姨歇斯底里的哭泣声:“我的儿啊,你这是要了你妈的命呀!”
她蓦地觉察出又什么不对,胡同口刚才停了不少车,她本来还奇怪是谁家来了亲戚,原来竟然都是朝着表姨家来的。她急切地推开众人,挤了进去。果然,表姨刘淑惠坐在地上哭天抢地,任婷居然也在家里。
任婷一边扶着母亲,一边也抹着眼泪,看到黄欣悦的时候,居然愤怒起来,上前就扬手掴了她一掌:“黄欣悦,你还知道回来呀?这个家白养你了,出了这么大的事,都找不到你的人影,你到底干什么去了?”
黄欣悦捂着脸,不解地问:“出了什么事?”
只见任婷忽然抽泣起来:“鹏鹏死了……被人捅了一刀,连肠子都流出来,死了两天了,被丢在郊区的一所鱼塘里,如果不是正巧有人去钓鱼,还不知道……”
“啊?”黄欣悦觉得心脏蓦地抽紧了起来,她不可置信地退了几步,摇头:“不可能……这怎么可能……发生了什么事?”
“就是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现在警察叫喊爸过去做笔录去了,现在暂时还不让我们见人,说是勘验完再让我们见面。”
黄欣悦软绵绵地走过去,想扶住表姨刘淑惠,不料表姨却挣脱了她的手,恨恨地说:“他到底不是你的亲弟弟,你才这么懈怠,我早就让你们姐妹两个多帮帮他,给他找个像样的工作,现在可好了,四处被人追债,还死于非命……让我这白发人送给黑发人,这可让我怎么活呀?”说完,又抽噎起来。
听到表姨将这一切责任推诿在自己这里,黄欣悦不知道该如何自辩。
“不要以为我是瞎子,告诉你,我可是过来人。你和那个顾明晨不清不白,还和一个长得英俊潇洒的年轻人在胡同里暧昧不清……我是亲眼看见了……我以为我会把你带好,没想到是功亏一篑,你到底是承继你的亲娘那狐媚子的妖性……我真是后悔,真不该留着你……”
黄欣悦惊呆了,看到任婷咬牙切齿瞪着自己说:“我早就告诉过你,顾明晨是我看上的男人,你不许和我抢……没想到,你还变本加厉了。妈都告诉我了,顾明晨不仅不许你辞职,还给你升职加薪了……你告诉我,你到底用了什么手腕,才让顾明晨对你死心塌地?”
“我没有……”黄欣悦委屈地咬着唇,很想告诉她们,自己已经有爱人了,不是顾明晨,但是她看到门外都是看热闹的人,不知道说了会不会有人相信,怕是流言更加漫天飞了。
“事实证据确凿,今天早上公司例会,已经宣布了你的事,难道你想否认?”
黄欣悦正想再解释自己一定不会再去公司任职的,忽然看到门外安静了下来,只见任婷的同学李鸿陪着姨父一前一后走进来。
不过几天没见,姨父的白发又增加了许多,他走得很慢,并没有说一句,只是一个人默默地走到院子里的太师椅上,无力地坐了下来。他那衰老的容颜与涣散的眼神,掩饰不知那发自内心的蚀骨的悲恸。
此刻,刘淑惠似乎凝聚了全身的气力,几步冲了过去,拉扯着丈夫的手,问:“怎么样?见到了吗?”
任文良点点头:“只是远远看了一眼,说是明天我们就可以去办手续领取尸体了。”
刘淑惠哀哀地看了一眼天空,顿时跌坐在地上,又嚎啕大哭起来。任婷也随着母亲啜泣起来,李鸿赶紧过来扶住任婷。几个街坊邻居都跑进来,将刘淑惠扶起,安置坐下,你一句我一句纷纷安慰劝说她要节哀顺变。黄欣悦也很担心表姨,但是不敢上前,只好一个人站在院子里人少的地方。
任文良长长叹息了一口气,哀声说:“谢谢他这些大伯大妈们怜悯,这孩子自小就不争气,现在是自作孽、不可活,我们这作父母的,也是尽了力了,既然是命,我们也就认了吧!”
邻居们又开始嗟叹和安慰。
忽然,刘淑惠的身子颤抖了几下,似乎被注入了一股邪恶的能量,她指着黄欣悦对任文良说:“你还好意思说,今天当着大家的面,我也不怕家丑外扬了,任文良,告诉你,都是你把我给逼的,你逼死了你儿子,不如现在也把我的命拿去,我受够了!”
任文良皱着眉头怒说:“都是你把他惯的,只知道宠溺,不教他做人,现在都是自食恶果,现在还怪谁呢?我们的都有错,现在也遭到惩罚了。”
刘淑惠凄厉地仰天大笑几声,又开始痛哭流涕地说:“这孩子虽然有些不太稳妥,但是并不是个不可救药的。如果你对他稍稍加些关心,和对待那个女人的女儿一样多花些心思教导他,他怎么会遭遇到难处都不敢回家,最后把自己给逼死了!你居然还说,都是他的错!任文良,我恨你,恨你一辈子都没有把心放在我和自己的亲生骨肉身上!”
“你胡说什么?”任文良听到妻子这样说,脸色涨红得和紫茄一般,颤颤巍巍地站起身来。
“我是什么你心里明白!”刘淑惠仿佛忽然醒悟了,一口气将积压在自己心头多年的恶气一并发泄出来,她指着黄欣悦冷笑,“实话对你说,我一看到她就想起那个女人,想起那个你得不到的女人。我从嫁给你之前,就知道你这辈子最厌恶剽窃别人的劳动成果,你曾经险些与你的师傅对抗,不学那临摹术,但是你最后却由于那个人改变了初衷。你这一辈子就只临摹了那一幅画,你废寝忘食,穷其所能,就是为了那个女人,你现在还不敢承认吗?你知道吗?我每次在你屋子里收拾出那些废纸的草稿纸,我都恨不得将它们都吃下去!”
任婷看到母亲如此哀绝,也忽然对自己的父亲说:“爸,我和妈一样,不喜欢那个女人和她的孩子,这也是我不愿意回家的原因。我小时候常常看到母亲人前强颜欢笑,背后悄悄抹眼泪,我就知道她这辈子,定然是受了极大的委屈!爸,是你,伤了我妈的心!”
她说着,忽然狠狠瞪起眼,朝着黄欣悦冲了过去,狠狠撕扯着她的头发,歇斯底里地拳打脚踢,边哭边骂起来:“如果不是因为你母亲和你的出现,我们这个家就会过的好好的,我妈她不会这么伤心,我弟弟也不会死!我恨死你了!”
黄欣悦没有躲避,她忍着肌肤上传来的撕心裂肺的疼痛,忍着被人撕扯的难堪,默默无语。她也记得表姨经常偷偷抹着眼泪,却不知道为什么,也许正因为她们所说,是自己的母亲和自己造的孽。如果真的躲不开这孽债,如果这样可以让表姨失去亲生骨肉的痛苦减轻一些,她愿意承受。
但是,她还没有来的及再思考下去,忽然听到任婷喊了一声:“爸!”
只见任文良冷着脸,重重地给了任婷一巴掌。这巴掌传递过来的声音在杂乱的人声中尤为清晰响亮,众人顿时都懵了。
任婷被父亲可怕的面孔惊吓住了,她捂着脸,两眼含泪,一步一步朝后退去。李鸿急忙冲上前,一把搂起她,将她迅速拉扯到角落里,柔声安慰起来。
任文良的表情非常凝重,他推开众人的阻拦,转身朝刘淑惠走过去,郑重地说:“淑惠,我知道你对我怨气很重,但是我没有对不起你,也没有对不起这个家,任鹏他有他的命数,我们只能教他走路,不能永远搀扶着他走路。他小时候,我让他去买白矾,他去看人家逗蝈蝈,白矾洒了一半还多。我让他学裱画,他嫌累,兑现慢。让他去学英语,结果他半途又废了跑去赌钱。我昧着良心,将那临摹画给了他,不就是为了救他?可是,他能体会到父母的苦心吗?”
刘淑惠被他的表情也震慑住了,忽然,她浑身抽动了几下,闭着眼便朝后倒了下去。这个紧急情况,把大家又给吓了一跳,立刻有人上去掐人中,有人上去搓手。邻居周大爷家的小儿子正在中医药大学读研究生,见到这情形,连忙上前在刘淑惠的人中、百会、合谷等穴位扎了上去,过了不久,只见刘淑惠才悠悠转醒。她嘴角抽动了两下,呼吸渐渐均匀,眼角又渗出几滴眼泪,但是还是不肯睁开眼睛。
任婷此刻也哭得几乎上不来气,躲在李鸿的胸前哽咽着。
黄欣悦看到任文良仍旧走过来对她说:“欣悦,你暂且先回避一下,她们母女两个是太伤心了,没有地方发泄,让你受委屈了,你先回你的公司去工作,等过些日子,她们的情绪渐渐回复过来再回家来,好好和她们聊一聊。”
这几句说完,黄欣悦终于抑制不住自己的眼泪流了下来。一个刚刚遭受了丧子之痛的父亲,一个洁身自好、素来注重好声名的男人,刚刚在众目睽睽之下,被妻子和女儿指责,那种渗入灵魂的悲恸该有多深,但是此刻,他还是顾念着自己的感受,这些关爱,让黄欣悦感受无地自容,感到难以承受这份恩情。
“姨父,我可以多知道些我父母和您的故事吗?”黄欣悦知道此刻并不适合说这些话,但此刻又是打开姨父心扉的最好时机,所以,她鼓起勇气问了出来。
任文良的眼神里流泄出一丝异样的光,慢慢点头:“好,我答应你,等办完了任鹏的丧事,我就好好说给你听。”
“您多保重……姨以为多保重……”
黄欣悦抹了一把眼泪,看到四处都是摇头叹气的目光,无奈,只好一步一步慢慢朝外走去。她真的不想离开,她只想在这个家最困难的时刻,和自己最在乎的家人,一起渡过,欢乐也好,悲伤也好,只要可以和家人在一起,什么样的苦她都可以承受。可是,现在的她,居然成了这个家最憎恶的人。
她想不开,这究竟是为了什么?母亲,如果你还在这个人世,可不可以回来,告诉你的女儿,这究竟是怎么样一段宿怨?过去的时光里藏着怎样凄婉难堪的往事?她的脑海里不停浮现出过去的点点滴滴,那间曾经遭遇过大火的中药店,就是夏长风的家,似乎也隐藏了什么难以洞悉的往事?她想得头疼欲裂,不知不觉快要走到胡同口的大街上。
“黄女士,又有您的快递。”她看到上次给自己送生日蛋糕的快递小哥正朝自己笑着,“上次的蛋糕比较重,这次就轻飘飘的,好像是一份文件。”
黄欣悦勉强控制住自己的情绪,对快递小哥说了声:“谢谢。”
她的手有些微微颤抖,但还是打开了那文件,她万万没有想到,那居然是一张法院的传票。原告就是上次到自己家裱画,被自己剔除掉纸张里的头发丝的男人,叫邓玉春,他告自己以裱画为名,用不正当手段换了他家的原画,他要求黄欣悦将他家的原画完整奉还,还要赔偿他因此次造成的经济损失与精神损失费五百万。
她觉得自己的视线有些模糊,前边似乎来来往往很多车辆,还有一个男人忽然出现,挡住了自己。她不知道,自己就这样朝地上倒去,只是残留的意识里,仿佛有人轻轻揽住了自己的腰身,轻轻叹息了一声。那声音有些熟悉,也有些惋惜与心疼的意味。
四周的树木与建筑物旋转起来,天地一片昏黑,她似乎渐渐进入了一个未知的世界。
 收藏
收藏  打赏
打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