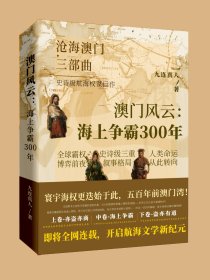第一章 迷而知返
烟花三月,水寒如昔,三两条木舟缓缓前行。十里长堤,路人寥寥,稀疏的林木开始返青,唯独林木中的鸟巢浓色逼人,视线广转,四周浅浅流淌着蠢蠢欲动的生机。
黄欣悦戴上白手套,将被撕成十数片的古画《疏林寒绿图》大致摆拼了一下,已然为作者的智慧叹为观止了。满眼的画里看不到一丝一毫绿意,但是只凭这些,已经足够感知到冰河瞬间顿开、春雁即将归来的美妙了。
很可惜,中间最显眼的地方,撕破了一个不大不小的洞。黄欣悦皱着眉头,这毁损情况比起先前她所裱过的古画来说,并不算严重,但是这画纸却十分难得,从纸的韧性、纤维与硬度来看,似乎与宣纸难分轩轾,但却分明有些不同。
黄欣悦的心中微微触动了一下,那地杆上有一道令人不易察觉的指痕。那是裱画师傅的习惯动作,每当做完最后一道工艺,用拇指轻轻掐一下,以便了解那纸张干燥的程度。她心中已经确定,这画无论是不是真迹,她都要回表姨家一趟,去找表姨父任文良了。因为,掐纸测湿度正是他多年来最惯常的动作之一。
“怎么?还真是你!”
黄欣悦抬头,看到表妹任婷一脸不可置信的模样,站在自己面前。她心中暗暗慨叹,冤家路窄,正是如此。表姨家的妹妹任婷恰恰就在这里工作,来前,她曾经祈祷最好不要遇到她,现在看来怎么都躲不过去了。
任婷实在是个漂亮的美人,黑亮的瞳孔,长长的睫毛,往下是比例正好而又坚挺的鼻子,白皙的皮肤点缀着性感饱满的红唇,一身拘谨的职业女装丝毫掩饰不住她的活力。但是,黄欣悦对这种逼人的艳丽有一种不由自主的避讳。
她没有抬头,只是轻轻应了一声:“实在对不起,接受这项工作,是我们公司的决定,我也必须遵守。”
她心中明明知道这句话对任婷有很大的冲击,但是,都这么多年了,既然改变不了她,也没必要非要将自己蜷缩起来,永远做一只埋起头来掩盖自己的鸵鸟吧!
任婷果然有些怒意:“好,既然你这样说,那我也告诉你,如果不是这幅画毁在了文道拍卖行,如果不是顾总念着与画作主人穆先生多年的交情,一定要修复这幅画,我还真是不愿意见到你。”
“我来这里也是公事公办,做完这份工作,我们就会和以前一样,不会见面了。”黄欣悦依旧低着头,视线集聚在那幅画上的笔法与功力上,即便是仿制品,这种笔力也是大师级的水平,是非常有价值的。
“你!”任婷先是有些气急败坏,然后便轻蔑地抱起手臂,说,“你知道这事有多严重吗?你知道你现在做的事会影响整个拍卖行的声誉吗?”
“我当然知道,这么大个拍卖行怎么可能出现假画呢?所以你们顾总经理一定要修复好它,如果有可能,最好是可以证明,它是不折不扣的真品。”
黄欣悦刚才已经听拍卖行的工作人员说,这画的作者为元代画家盛懋,之所以被古画鉴定家高教授鉴定为假画的理由,并不是这幅画的画风与盛懋现存的其他作品不匹配,而是高教授说,只要不能证明盛懋确实画过此画,那它就是伪作。但画作主人穆先生说,他多年品读古画,也专门研究过盛懋的作品,这明明就是他的真迹,没有证据证明它是假画,就不要信口雌黄。因此,两位先生争得面红耳赤,互不相让,直到最后被激怒的穆先生居然几把撕毁了它。
黄欣悦虽然不敢确定这画的真伪,但她却知道,如果表姨父任文良亲笔裱过这画,那它就有可能是真的,因为表姨父生平痴迷裱画,早些年就停薪留职,在家里专门做起裱画的生意来,他生平最恨造假,也只裱真品。即便很多人用重金酬谢,他也会将其拒之门外,所以黄欣悦对这幅画是非常重视的。
任婷看到黄欣悦平静如水,并没有丝毫气怒,只好跺了跺脚,不满地说:“真没想到,这几年你可长本事了,变得伶牙俐齿的,再也不和以前在家里那样装柔弱了。”
“任总监,如果我们要谈公事的话,我想对你说的是,请带我去见一下你们顾总。”
“你真是蹬鼻子上脸,居然还想见我们顾总?我是这里的行政总监,你有什么话和我说就可以。”
“刚才你也说过,这件事关系着拍卖行的声誉,所以不能等闲视之,我需要亲自和顾总谈一些专业性的话题,如果耽搁了,这责任你我可都担不了。”
“你!”任婷的花容月貌瞬间扭曲了,但是,她思考了片刻,只好冷“哼”了一声,转身朝前走。
黄欣悦的嘴角淡淡咧开,知道任婷顾忌的不仅仅是这句话,而是半年前她辞了中学英文教师的工作,用尽心机才进入这拍卖行,这件事表姨父任文良并不知晓。黄欣悦为了息事宁人,也就装作不知道。
任婷的高跟鞋磕在锃亮光滑的地板上,发出清脆的声音。
黄欣悦小心翼翼抱着放着那张画的长盒子,看墙壁镶嵌着很多青花瓷片,横截面上浸透了岁月的痕迹,即便它们到处是裂纹,但是呈现出来的那静谧高贵的色调与内在的深沉,在这个充满了物欲的时代,都是一片清流。她想,今人喜爱这古物的缘由也是因为那独一无二的美感和在岁月时光中延续下来的怀旧情怀罢!她猜不到自己即将面对的是什么样的人,也不知道对方会怎么解读自己的行为,但是她已经暗暗作了决定,自己要做一件令人匪夷所思的事了。
此刻,顾明晨正蹙着眉头,叮咛着负责外事公关的负责人方宁:“方经理,务必要将这件事的影响降低到最低,从今天开始,拍卖行不接受一切电话或者来人采访,如果在网络上出现相关信息,一定要尽管与网站联系,用尽一切办法都要删除。还有,最好是防患于未然,不让这种事发生,你们应该明白我的意思?资金方面,我这里承诺,会给予最大的支持,但是一定不能让我失望……”
他挥了挥手,让方宁出去了。但是,他知道自己的心境并没有平复,这一切发生得实在匪夷所思,素来稳妥的教授不知道为什么会失控,穆先生更是出乎意料,竟然将画给毁掉。
忽然,听到轻轻敲门的声音与甜腻的女性嗓音传了过来:“顾总,我们的古画修复合作方岁月流光艺术发展有限公司代表黄欣悦女士想见您。”
“进来吧!”
顾明晨的视线出现了一个身材瘦弱,五官还算清秀的短发女子,她怀里抱着的正是那只装有《疏林寒绿图》的紫檀木盒。
这个叫黄欣悦的女人看到顾明晨,眼神淡淡飘了过来,如同清风明月一般,不起任何涟漪。只是片刻,她的眼神又瞥向站在一旁的任婷。
顾明晨非常明白这个女人的意思,于是挥手说:“任总监,你先去给我准备一下明天的行程计划,这里暂时不需要你了。”
任婷脸上划过一份不易察觉的不满,扭身离开了。
顾明晨蹙紧眉头,直视着她说:“现在没有人,可以说了吧?”
黄欣悦点头,将盒子轻轻放下,打开,小心翼翼地指取出那幅《疏林寒绿图》,说:“这样一幅不能确定是真伪的画,还能够得到贵行的重视,足已经说明它非同一般,但是,我想说的是,我恐怕不能完成贵行的委托,我回去会和我的公司解释,并取消与贵行的合作。”
“你说什么?”顾明晨的身子僵硬起来,他动了动,按捺住内心的不快,“黄女士,有什么话不如开门见山,大可不必先上纲上线。”
“好,那我就打开天窗说亮话了,如果我看的不错,这画难以完成装裱的原因是它所用的纸张为传说中元代的古白鹿纸……现在难以找到一模一样的纸张,所以……”
“你的意思是,这画是真品?既然是元代的纸张,且不可复制,就说明一定是对的?”
“不!”黄欣悦再次摇头,“还有一种可能,就是装裱的人拥有这种古纸……”
顾明晨起身,诧异地说:“你说什么?这白鹿纸真的还有余量存世?”
黄欣悦淡笑:“这也是我和顾总一样心存疑虑的地方,所以我需要时间去探寻,一周后,我会给您答复,可以吗?”
顾明晨愣了一下,忽然叉着腰放声大笑:“黄女士,你是在和我开玩笑吧?你可知道,这画如是真品,价值多少,我拍卖行每天都要有多少资金流水在运营?一周?一周的时间,我这里怕是几个亿就打了水漂了。还有,现在到处都是虎视眈眈,恨不得我垮台的竞争对手,这幅画要是真有个什么纰漏,我这里失去的可是信誉!信誉是什么?是无形资产,价值不可估量,说不定我这个拍卖行就因为这件事成为众矢之的,前期所有的努力都化为泡影!你说,我该怎么回复你?”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顾总这样实在难为人了。”黄欣悦将古画装进盒子里,推到顾明晨面前,“这么珍贵的东西还是暂且先保存在这里吧,如果有幸可以找到白鹿纸,那么它也许有救,如果没有,那请恕我无能为力了。”
顾明晨一怔,觉得自己还真是小看眼前这个女人了,她表面恭敬,其实没有半分退让,暗自藏了无数锋利的刀刃,短短几句话,就让顾明晨失去了往日的冷静。于是,他冷笑:“很好,你可以离开这里,我立刻给你们公司电话,让他们再换一名修复师来,不过,在这之前,我要先扣你们百分之十的延时履约费。”
黄欣悦并没有因为顾明晨的话慌乱,她缓缓地将手套摘了下来,放进包里,说:“顾总,对不起,我失礼了。不过,我想说的是,我们公司并没有违反约定,只是在合同执行过程中忽然出现了不可抗力,这纸张是裱画的魂,没有适合的纸张来裱画,怕是会毁的一无所有。还有,我们公司现有三位修复师,一位出国度假了,一位刚刚生了女儿还不足满月,现在恐怕只有我一个将就着用了。所以,您现在说的实在有些强人所难了,您在这行业做了这样久,也算是行家了,自然懂得此中道理。”
顾明晨手里抓住了一只空心玻璃杯,不知不觉用了些力,忽然听到“啪啦”一声,只见内层的玻璃竟然碎裂了,他扔掉杯子,轻轻抽了一张纸巾,抹去了涌出来的血迹。他抬头看到,对面的女人仍旧用淡漠的眼神看着自己,心头蓦地被刺了一下。从来在谈判桌上自己都是主导,但是此刻在这女人面前,他觉得这状况似乎有些失控。
于是,他轻咳一声,说:“我们公司和你们岁月流光艺术发展有限公司是签过长期合作合同的,这合同是有法律效力的,履行合同是你们公司的义务,现在无论你找多少理由,还是要履约的。”
黄欣悦眯着眼皮,回答:“我本来是个公私分明的人,不想在工作中涉及个人隐私,但现在顾总既然不肯通融,那我也只好自报家门了。从这画的装裱风格上看,是出自我的表姨父任文良之手,他虽然只是美术老师出身,但是曾经得到过民间艺术大师的教授,多年对裱画深有研究,在古画裱画界也算是一个资深的元老了。所以我想回去询问一下,这画真假自辩。请问顾总,这样的解释您满意了?”
“任文良?”顾明晨虽然没有听说过这个名字,但他知道民间有很多业界高手,暂且不论这《疏林寒绿图》是真是假,也不论其绘画功力如何高深莫测,他看的出来,仅凭这裱画的技艺就实在是超凡脱俗,自成一派。他沉思了片刻,说:“怪不得……那好,就给你一周时间,然后一定要有个说法,否则我不但中止合同,还要索赔!”
黄欣悦不满地看了一眼顾明晨,暗道这商人的嘴脸真是变化无常,她点头说:“好,那顾总我出去了。”
顾明晨挥挥手,瞪着她开门离开,这才气鼓鼓地喝了一杯咖啡。他低头看到桌子上那幅画,不禁有些觉得奇怪,又将它打开细细窥视一番。那画里的水木皆生动逼真,即便是孤寂,也不知不觉充满了一种向上的力量,这力量到底出自哪里?他又看了看盛懋的资料,其人在当朝并不算上顶级大师,但他的作品吸取了宋元两代山水画的特点,贴近自然,笔墨图式复杂多样,不可小觑,古画界对其流传于世的作品也颇有微词,但是正是这种不同,反倒提升了其内在的价值。这《疏林寒绿图》也确实符合他素常的书画作风,但是确实没有人可确定他到底是不是盛懋亲笔。
顾明晨用手指敲着桌面,不小心触动了刚才的伤口,他看了看自己的手指,又渗出一丝血迹,不由苦笑一声。对于拍卖行来说,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他不敢肯定,这个貌不惊人的女人,真的可以撑起这一切。但是目前也没有特别好的办法,他按捺住内心的浮躁,不得不把所有的一切都压在这个女国画修复师身上。他暗暗捶了几下有些发紧的额头,眼睁睁看着她的身影渐渐消失。
黄欣悦没有再见任婷,因为她要去的地方,是任婷最不想回去的家,她怕稍有不慎会触动任婷内心的底线,于是独自悄悄出了文道拍卖行的大门。外边的风还是有些清冷,她捂着脸深深呼吸了一口。没有人知道,她是怎样拼命抑制自己内心的翻涌,她怎么敢相信,姨父所用的裱画纸张居然是传说中的白鹿纸?小时候和任婷、任鹏追逐打闹,偷偷翻遍姨父的书柜,从来没有看到过这种纸张,她不敢相信自己的判断,不敢相信姨父会为了一幅假画费尽心力装裱,这是藏在她心头难以述说的东西,所以她觉得一刻都不能迟缓,要早些见到姨父。
手机忽然响了起来,是任婷。黄欣悦犹豫了片刻,还是按下了键。
“黄欣悦,你也不打个招呼就离开了,我这话还没说完呢!记住啊,不许告诉家里我在这里上班,如果我知道是你说的,我一定跟你没完!”
黄欣悦想了想,说:“好,我答应你。如果我说了,你可以和小时候一样用脸盆泼我一头脏水!”
对方传来“哼”的一声,然后就挂断了,只听到滴答滴答的忙音。
她从来都记得很清楚,那是初冬一次大雪后,她的语文考了全班第一名,当她兴冲冲地抱着奖状回家,刚打开门,忽然觉得头上被什么东西撞了一下,瞬间一脸冰冷的臭水灌入了脖颈里。她看到一只破旧的牡丹花搪瓷盆扣在地上,散发着恶臭的味道。她打了一个冷颤,看到任鹏嬉皮笑脸地跳了出来,趁她不注意一把夺过她手中的奖状,喊着:“姐姐,怎么样?我说她肯定中招,哈哈,还拿着奖状想讨好爸妈呢?”
黄欣悦看到任婷拿着一把木梳,梳着自己的一头长发,皱眉说:“还拿着奖状想回家显摆?不过,让你失望了,我爸妈今天出门看望老朋友去了,不在家,你这张破纸就没人看了。”她忽然得意地笑了笑,几下就将那奖状撕了几把,往地上一扔,然后扬长而去。
任鹏又蹦跳着,朝黄欣悦挤着鬼脸:“我看你这回找谁哭诉?我看你没事老是逞能?你可臭死了,赶紧离我们远点!”
黄欣悦浑身透凉,她看到任鹏与任婷的脸压在窗户玻璃上偷偷笑着,自己的奖状被撕得到处飞扬,泪水蓦地流出来,于是她迎着不时袭来的寒风,追着将那些纸屑都捡了起来。
天色渐渐暗黑,屋外被雪映衬得如同白昼,任文良与刘淑惠还没有回来,她只好自己把衣服换了、洗了,然后到了任文良的裱画室里。那里还摆放着任文良早上用过的半瓶浆糊。曾经有无数次,她看到姨父就是这样带着围裙,将一大团面揉合,然后醒上个把钟头,放水洗去面筋,再添加上自己独特的草药配方,熬成可以装裱用的浆糊。
她找了一张被任文良废弃的白纸,将奖状的碎片一一拼接起来。想着姨父平常说的话:“可别小看这两把刷子,千古流传的手艺都在这里。”她学着姨父的样子,将那些碎片用浆糊一一粘贴,但是中间少了一块,就是缺少写着黄欣悦名字的那一块。黄欣悦抹了几把眼泪,在姨父废弃的碎纸里找了一块和奖状硬度差不多的纸,剪成和破洞差不多大小的面积,开始贴补起来。但是那纸张的颜色还是相差了很多,黄欣悦的小脸哭得有些皴了,摸上去还有些微微疼痛。但是,她只是想将它拼好,她只想要一张完整的奖状。
她拿起衣姨父的毛笔,用些红色的颜料将那块补洞的纸轻轻描上颜色,还学着用毛笔写着自己的名字,但是她无论如何也驾驭不了那支笔,于是她一边哭,一边继续描着……就这样,她不知不觉睡着了。等她醒来,就已经睡在自己的床上了。
她的意识是模糊的,感觉自己唇齿间还残留着药物的苦味,忽然听到姨父训斥任婷与任鹏的声音:“怎么回事?姐姐病了你们两个怎么无动于衷?我平时是怎么教你们的?”
她还听到表姨的声音:“孩子们还小呢,自己能把自己照顾好就不容易了,现在欣悦这不就是个感冒发烧,过几天就好了,不要成天和凶神恶煞似的,孩子们都和你不亲了。”
“哼,都是你给惯的。”
黄欣悦感到一双非常粗糙的大手在自己头上摸了摸,说:“这药还真是管用,欣悦,好好睡一觉,明天就好了。”
她很想和姨父说句话,但是什么都说不出来,意识又模糊了。
再次醒来,她觉得自己的头清醒了很多。她看着四周,到处静悄悄的,忽然看到桌子上有一盘芝**仁点心,下边还压着一张纸。那张纸飘落下来,她捡起来,原来是自己那张奖状,最令人惊奇的是,这张奖状完整如昔,竟然看不出一丝一毫曾经破碎过的痕迹。
她不敢置信地揉了揉眼睛,确实是写着“黄欣悦”同学名字的那张奖状,“黄欣悦”那三个字与其他的字浑然一体,根本看不出来是修补过的。
她知道这一定是姨父亲自修复的,但是这种神奇的技艺,从此就在黄欣悦幼小的心灵留下了深深的痕迹。
午后的阳光是一天中最暖的了。黄欣悦站在通往表姨家的胡同口,这条胡同很深,与正街相通,胡同口放着一辆破旧生满了锈、只有一只轮子的老自行车,园艺工人没有将它清理出去,而是借物造景,将它给那些藤本蔷薇做了支撑。一株有些年岁的国槐在阳光下拉出了长长的影子,那稀疏的枝干隐隐露出几分绿意。黄欣悦帮着往胡同里边骑去的快递三轮,捡了一件掉落的快件,快递小哥连连说了几声“谢谢”,让黄欣悦有些羞怯起来。
表姨家在胡同的尽头,那扇门似乎刚刚刷了一层新漆,黄欣悦犹豫了片刻,还是推开了那扇门。她的童年,是过去时光里难以述说的一段存在。她三岁那年,父亲忽然死去,母亲将她带到这里,从此这里就盛满了她童年全部的记忆。表妹任婷、表弟任鹏后来接连出生,这个家就是在表姨刘淑惠的抱怨声、表姨父任文良的叹气声中流淌着日子的琐碎。
虽然这些年她不知道母亲去了哪里,母亲为什么就她寄放在这里一去不返,但是她察觉的出来,表姨父是一直护佑着自己的,并没有苛待自己,反而比对自己的亲生子女还要好。他曾经为黄欣悦凑够了攻读研究生的生活费与学费,不惜日夜赶工,将自己的手给折腾肿了许多天才痊愈。而和她有着血缘关系的表姨刘淑惠却对她不冷不热,她只是一味溺爱着自己的两个孩子,因此任鹏高考落榜后,就再也没有复读。他后来在一家房地产公司做保安,本来也能过上安生日子,但是他却始终没有让父母省下心,打架酗酒折腾了几次,被公司辞退,只好终日游荡闲赋。
黄欣悦想着,迈开步子朝里走着。院子里很安静,也收拾得非常利落。东南角是一大簇黄槽竹,这是北京庭院里最常见的竹子品种,自从表姨家住在这里以来,便一直都长得很旺势,春光明媚的日子里,这片竹影斑驳,浓淡相宜,也因为有了它们,无形中给庭院增添了一抹生机。一张老榆木桌子,几把老竹藤椅子是平常家人一起在庭院里吃饭用的,也都看不到什么灰尘。表姨刘淑惠似乎不在家。她看了看正屋墙壁上的一只老雕花木的钟表,这个时辰应该是表姨出去买菜的时间,估计也快回来了。
她的脚步很轻,不敢发出声音。每当这个时辰,是姨父潜心工作的时刻,她站在窗口,看到姨父任文良身上围着围裙,手中拿着一把大刷子,正专心地在一张三尺多长的纸上用力刷着。
黄欣悦很熟悉这道工序,这道工序叫托复背。就是要给裱好的画上再一层或多层的纸。这纸不能太薄,也不能太厚。不可以用熟纸、绢帛、毛边或者报纸来代替,否则日久易破,也会有损原作。但见眼前一位鬓角早生华发的老人,正扬起一张棉连纸,仔细覆盖在画上,然后熟练地刷上浆糊,然后又扯出一张纸,覆盖在上边,再继续刷下去……阳光中,瘦削的身影与扬起的纸张融为一体,整个看起来便是人与纸的美妙共舞。
黄欣悦看到姨父将做好的复背纸,轻轻刷在一张书画作品上,方才轻轻舒了一口气。看到这里,黄欣悦进门,轻轻喊了一声:“姨父。”
“欣悦,你回来了?”任文良看到黄欣悦进门,紧绷的脸上骤然舒缓了许多,看的出很开心,他笑着说:“赶紧,帮我一下。”
黄欣悦点头,和过去一样,帮助表姨父小心翼翼扶住那画,慢慢讲那画贴到墙上。
任文良又拿出那把鬃刷,屏住了呼吸,顺着纸张的纤维方向轻轻地刷了过去,在覆背纸四边抹上浆糊,最后将复背纸与画固定在墙壁上,才终于完全放松下来。此刻,墙壁上的画带着特殊的药香与未曾干涸的浆糊味道,险些将黄欣悦的眼泪勾了出来。
耳边听到任文良如获重视般地又舒了一口气:“现在天气越来越暖和了,我这心里就踏实了,不怕它给崩了,到时候没法交代。”
黄欣悦轻轻吸了一下鼻子,说:“姨父,您裱了这么多年的画,真是万物一失吗?真的没有出过差错?”
任文良“哼”了一声:“我也不是大罗金仙,怎么可能没有出过差错?当年……”
黄欣悦正想继续听下起,忽然听到任文良顿了一下,似乎想起了什么,不再往下说了。
这是许多年来黄欣悦最习惯的场景了,表姨父本来就是个话不多人,只是偶而心血来潮,才会坐下来喝几杯酒,每次都是表姨陪着他喝,表姨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文良,你有什么话不要闷在肚子里,不如和我说一说。”任文良总是应一句:“老夫老妻了,都半辈子了,还说个啥呀!”说到这里便睡过去了,只留下表姨一个人说:“还说什么老夫老妻,就是半辈子了又能怎么样?我只是想听你一句真话,我过分吗?可惜了,我这头发都白了,也等不着,看来是我从上辈子就欠了你吧!”
每当想起小时候这些场景,成年的黄欣悦似乎明白了些什么。表姨这辈子心里只有表姨父一个人,但是,表姨父的心思难以捉摸,也似乎在他默默劳作的漫长岁月里,还曾经有过一段旖旎的回忆,但是,黄欣悦还没有想透,那到底是什么。
她听母亲说过,表姨与表姨父这门亲事,是自己的外祖父颜祖山亲自做的媒,表姨是外祖母亲妹妹家最小的一个女娃,生的漂亮大气,于是便托付外祖父将她嫁给了自己的二弟子任文良,表姨父之前在中学教书,表姨就在学校的食堂里工作,现在退休后,更是一心意打理家事。
正想着,听到门忽然开了,刘淑惠提着一只老母鸡回来,那只鸡的腿和翅膀都被白布带绑着,还试图挣扎着,听到她一边走一边骂:“你这是贼心不死呀!都死到临头了,还折腾什么,认命就是了。”
黄欣悦站直了身子,朝刘淑惠喊了一声:“姨。”
刘淑惠怔了一下,似乎有些吃惊,但是很快就镇定如常了:“回来了?怎么也不提前打个电话说一声?”
任文良看着那幅画,点了点头,说:“这是她自己的家,想什么时候回就什么时候回,打什么电话?这不,还是她姨有先见,连老母鸡都买回来了,赶紧收拾一下,炖一锅红烧鸡炖土豆,欣悦最爱吃这口了。”
刘淑惠的表情僵了一下,低声说:“你不是总说自己的手脚有些不利落吗?我是听说用天麻炖老母鸡可以治你这毛病,所以……”
任文良大手一挥,将腰上的围裙摘了下来,喝了一杯桌子山早已经放凉了的菊花茶,“嘿嘿”一笑,不以为然地说:“别提那些捕风捉影的话,要是真吃了只老母鸡,人就利落了,那些大医院不早就关门了?”
黄欣悦忧心忡忡地看了任文良一眼,只见他不停地捋着自己的食指,问:“姨父,您的手?”
任文良“哈哈”一笑,说:“没什么,就是觉得近日有些发麻,我天天干的是这个裱画的精细活,这手指头想坏了都没那种可能。”
刘淑惠“哼”了一声:“看你逞能的!要不是看你成天辗转反侧,半夜老起来捶腿搓手的,我才不可怜你呢!”
“别说了,赶紧烧壶开水,烫了拔毛,好不容易孩子回来的,听说我,别放那什么天麻,炖土豆。”
黄欣悦连忙摆手:“不,姨父,我现在在外边工作,最注重形象了,不敢吃太多,这个老母鸡油太大,我可不敢吃,我有些蔬菜就可以了。”
任文良瞪眼:“什么?怎么这口气和任婷似的?可千万别学她,光想着什么减肥漂亮什么的,成天描眉画眼的,穿着都是什么奇装异服呀?每次一回胡同,别人都当怪物一样看着她,她怎么也不知道寒掺呢?”
黄欣悦听到又把任婷给扯出来了,表姨刘淑惠的脸色有些怪异,连忙打断了任文良的话:“我来做吧!”
任文良摇头:“淑惠,你去做饭,欣悦的手现在也是做精细活的,不要让她做这些琐碎的家务事了,你就代劳吧!听我的,炖土豆。来,欣悦,到里屋去,我有话对你说。”
任文良的书房是院子里的西耳房,最大的一间厢房是他的工作室,其他的是三个孩子的屋子,所以只剩下这一间耳房可以当书房了。此刻,大概是下午四点多了,光线已经有些昏暗了。任文良的书桌上摆放着一幅破旧的古画。
他一边摸了摸膝盖,一边坐了下来,说:“欣悦,我知道你回来肯定是有事要问我,有什么事就说吧,不要吞吞吐吐的。”
黄欣悦的鼻腔里忽然涌出一股酸楚的味道,她轻轻吸了一口气,说:“姨父,我见到了一幅画,那幅画的味道好熟悉。”
“什么画?是画得味道还是装裱的味道熟悉呀?”任文良一边问一边拿着放大镜看着那幅画中间破的一个洞,似乎在深深思考,下边的工序应该怎么做,才能将它完好无缺的补上。
黄欣悦闭了下眼又睁开,鼓起勇气说:“您常常说,这好画是三分画七分裱,但是我看到的这幅画不仅仅从裱功上看登峰造极,那画工也是非同小可,还有最奇怪的是,那张裱画用的纸,我从来见过。”
听到这里,任文良“哦”了一声,抬起眼皮看了看黄欣悦窘迫的表情:“孩子,你想说什么?”
“我”,黄欣悦鼓足了勇气,终于说出了自己心里的疑问,“我不懂,姨父您为什么会违背初衷,是什么力量让您会耗尽心力裱一幅赝品?”
任文良的神情凝重起来:“你说什么?”
“对,那幅画是元代盛懋的《疏林寒绿图》,这画工确实是盛懋擅长的笔法,但是如果我没有猜错,我母亲当年托付给您的就是这幅《疏林寒绿图》,我真的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如果这画是赝品,那么这画又是谁画的?如果是真品,那……”
黄欣悦很想质问任文良为什么会将母亲的画流失出去?但她看着任文良放下手里的放大镜,皱纹波动,表情凝重,扶着自己的官帽椅,缓缓地坐了下去,只好抿了抿嘴,不敢再说下去。
只见任文良的眼神浑浊迷离,他看着窗口,似乎陷入了难以名状的沉思中,良久,他叹了口气:“孩子,你是在责怪我吗?”
“不,姨父,我感激您对我的养育之恩,我并没有责怪您的意思,我只是想知道真相。”
“真相?”任文良的嘴角微微咧开,那笑容非常复杂深邃,“孩子,你长大了,我也该对你有个交代了。你说得不错,当年你母亲把你和那幅画托付给我,并告诉我,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可以将那幅画变卖,以解燃眉之急。”
“那,您遇到了什么样的燃眉之急?”黄欣悦没有想到自己这话就这样轻而易举地从嘴边溜了出来。
黄欣悦戴上白手套,将被撕成十数片的古画《疏林寒绿图》大致摆拼了一下,已然为作者的智慧叹为观止了。满眼的画里看不到一丝一毫绿意,但是只凭这些,已经足够感知到冰河瞬间顿开、春雁即将归来的美妙了。
很可惜,中间最显眼的地方,撕破了一个不大不小的洞。黄欣悦皱着眉头,这毁损情况比起先前她所裱过的古画来说,并不算严重,但是这画纸却十分难得,从纸的韧性、纤维与硬度来看,似乎与宣纸难分轩轾,但却分明有些不同。
黄欣悦的心中微微触动了一下,那地杆上有一道令人不易察觉的指痕。那是裱画师傅的习惯动作,每当做完最后一道工艺,用拇指轻轻掐一下,以便了解那纸张干燥的程度。她心中已经确定,这画无论是不是真迹,她都要回表姨家一趟,去找表姨父任文良了。因为,掐纸测湿度正是他多年来最惯常的动作之一。
“怎么?还真是你!”
黄欣悦抬头,看到表妹任婷一脸不可置信的模样,站在自己面前。她心中暗暗慨叹,冤家路窄,正是如此。表姨家的妹妹任婷恰恰就在这里工作,来前,她曾经祈祷最好不要遇到她,现在看来怎么都躲不过去了。
任婷实在是个漂亮的美人,黑亮的瞳孔,长长的睫毛,往下是比例正好而又坚挺的鼻子,白皙的皮肤点缀着性感饱满的红唇,一身拘谨的职业女装丝毫掩饰不住她的活力。但是,黄欣悦对这种逼人的艳丽有一种不由自主的避讳。
她没有抬头,只是轻轻应了一声:“实在对不起,接受这项工作,是我们公司的决定,我也必须遵守。”
她心中明明知道这句话对任婷有很大的冲击,但是,都这么多年了,既然改变不了她,也没必要非要将自己蜷缩起来,永远做一只埋起头来掩盖自己的鸵鸟吧!
任婷果然有些怒意:“好,既然你这样说,那我也告诉你,如果不是这幅画毁在了文道拍卖行,如果不是顾总念着与画作主人穆先生多年的交情,一定要修复这幅画,我还真是不愿意见到你。”
“我来这里也是公事公办,做完这份工作,我们就会和以前一样,不会见面了。”黄欣悦依旧低着头,视线集聚在那幅画上的笔法与功力上,即便是仿制品,这种笔力也是大师级的水平,是非常有价值的。
“你!”任婷先是有些气急败坏,然后便轻蔑地抱起手臂,说,“你知道这事有多严重吗?你知道你现在做的事会影响整个拍卖行的声誉吗?”
“我当然知道,这么大个拍卖行怎么可能出现假画呢?所以你们顾总经理一定要修复好它,如果有可能,最好是可以证明,它是不折不扣的真品。”
黄欣悦刚才已经听拍卖行的工作人员说,这画的作者为元代画家盛懋,之所以被古画鉴定家高教授鉴定为假画的理由,并不是这幅画的画风与盛懋现存的其他作品不匹配,而是高教授说,只要不能证明盛懋确实画过此画,那它就是伪作。但画作主人穆先生说,他多年品读古画,也专门研究过盛懋的作品,这明明就是他的真迹,没有证据证明它是假画,就不要信口雌黄。因此,两位先生争得面红耳赤,互不相让,直到最后被激怒的穆先生居然几把撕毁了它。
黄欣悦虽然不敢确定这画的真伪,但她却知道,如果表姨父任文良亲笔裱过这画,那它就有可能是真的,因为表姨父生平痴迷裱画,早些年就停薪留职,在家里专门做起裱画的生意来,他生平最恨造假,也只裱真品。即便很多人用重金酬谢,他也会将其拒之门外,所以黄欣悦对这幅画是非常重视的。
任婷看到黄欣悦平静如水,并没有丝毫气怒,只好跺了跺脚,不满地说:“真没想到,这几年你可长本事了,变得伶牙俐齿的,再也不和以前在家里那样装柔弱了。”
“任总监,如果我们要谈公事的话,我想对你说的是,请带我去见一下你们顾总。”
“你真是蹬鼻子上脸,居然还想见我们顾总?我是这里的行政总监,你有什么话和我说就可以。”
“刚才你也说过,这件事关系着拍卖行的声誉,所以不能等闲视之,我需要亲自和顾总谈一些专业性的话题,如果耽搁了,这责任你我可都担不了。”
“你!”任婷的花容月貌瞬间扭曲了,但是,她思考了片刻,只好冷“哼”了一声,转身朝前走。
黄欣悦的嘴角淡淡咧开,知道任婷顾忌的不仅仅是这句话,而是半年前她辞了中学英文教师的工作,用尽心机才进入这拍卖行,这件事表姨父任文良并不知晓。黄欣悦为了息事宁人,也就装作不知道。
任婷的高跟鞋磕在锃亮光滑的地板上,发出清脆的声音。
黄欣悦小心翼翼抱着放着那张画的长盒子,看墙壁镶嵌着很多青花瓷片,横截面上浸透了岁月的痕迹,即便它们到处是裂纹,但是呈现出来的那静谧高贵的色调与内在的深沉,在这个充满了物欲的时代,都是一片清流。她想,今人喜爱这古物的缘由也是因为那独一无二的美感和在岁月时光中延续下来的怀旧情怀罢!她猜不到自己即将面对的是什么样的人,也不知道对方会怎么解读自己的行为,但是她已经暗暗作了决定,自己要做一件令人匪夷所思的事了。
此刻,顾明晨正蹙着眉头,叮咛着负责外事公关的负责人方宁:“方经理,务必要将这件事的影响降低到最低,从今天开始,拍卖行不接受一切电话或者来人采访,如果在网络上出现相关信息,一定要尽管与网站联系,用尽一切办法都要删除。还有,最好是防患于未然,不让这种事发生,你们应该明白我的意思?资金方面,我这里承诺,会给予最大的支持,但是一定不能让我失望……”
他挥了挥手,让方宁出去了。但是,他知道自己的心境并没有平复,这一切发生得实在匪夷所思,素来稳妥的教授不知道为什么会失控,穆先生更是出乎意料,竟然将画给毁掉。
忽然,听到轻轻敲门的声音与甜腻的女性嗓音传了过来:“顾总,我们的古画修复合作方岁月流光艺术发展有限公司代表黄欣悦女士想见您。”
“进来吧!”
顾明晨的视线出现了一个身材瘦弱,五官还算清秀的短发女子,她怀里抱着的正是那只装有《疏林寒绿图》的紫檀木盒。
这个叫黄欣悦的女人看到顾明晨,眼神淡淡飘了过来,如同清风明月一般,不起任何涟漪。只是片刻,她的眼神又瞥向站在一旁的任婷。
顾明晨非常明白这个女人的意思,于是挥手说:“任总监,你先去给我准备一下明天的行程计划,这里暂时不需要你了。”
任婷脸上划过一份不易察觉的不满,扭身离开了。
顾明晨蹙紧眉头,直视着她说:“现在没有人,可以说了吧?”
黄欣悦点头,将盒子轻轻放下,打开,小心翼翼地指取出那幅《疏林寒绿图》,说:“这样一幅不能确定是真伪的画,还能够得到贵行的重视,足已经说明它非同一般,但是,我想说的是,我恐怕不能完成贵行的委托,我回去会和我的公司解释,并取消与贵行的合作。”
“你说什么?”顾明晨的身子僵硬起来,他动了动,按捺住内心的不快,“黄女士,有什么话不如开门见山,大可不必先上纲上线。”
“好,那我就打开天窗说亮话了,如果我看的不错,这画难以完成装裱的原因是它所用的纸张为传说中元代的古白鹿纸……现在难以找到一模一样的纸张,所以……”
“你的意思是,这画是真品?既然是元代的纸张,且不可复制,就说明一定是对的?”
“不!”黄欣悦再次摇头,“还有一种可能,就是装裱的人拥有这种古纸……”
顾明晨起身,诧异地说:“你说什么?这白鹿纸真的还有余量存世?”
黄欣悦淡笑:“这也是我和顾总一样心存疑虑的地方,所以我需要时间去探寻,一周后,我会给您答复,可以吗?”
顾明晨愣了一下,忽然叉着腰放声大笑:“黄女士,你是在和我开玩笑吧?你可知道,这画如是真品,价值多少,我拍卖行每天都要有多少资金流水在运营?一周?一周的时间,我这里怕是几个亿就打了水漂了。还有,现在到处都是虎视眈眈,恨不得我垮台的竞争对手,这幅画要是真有个什么纰漏,我这里失去的可是信誉!信誉是什么?是无形资产,价值不可估量,说不定我这个拍卖行就因为这件事成为众矢之的,前期所有的努力都化为泡影!你说,我该怎么回复你?”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顾总这样实在难为人了。”黄欣悦将古画装进盒子里,推到顾明晨面前,“这么珍贵的东西还是暂且先保存在这里吧,如果有幸可以找到白鹿纸,那么它也许有救,如果没有,那请恕我无能为力了。”
顾明晨一怔,觉得自己还真是小看眼前这个女人了,她表面恭敬,其实没有半分退让,暗自藏了无数锋利的刀刃,短短几句话,就让顾明晨失去了往日的冷静。于是,他冷笑:“很好,你可以离开这里,我立刻给你们公司电话,让他们再换一名修复师来,不过,在这之前,我要先扣你们百分之十的延时履约费。”
黄欣悦并没有因为顾明晨的话慌乱,她缓缓地将手套摘了下来,放进包里,说:“顾总,对不起,我失礼了。不过,我想说的是,我们公司并没有违反约定,只是在合同执行过程中忽然出现了不可抗力,这纸张是裱画的魂,没有适合的纸张来裱画,怕是会毁的一无所有。还有,我们公司现有三位修复师,一位出国度假了,一位刚刚生了女儿还不足满月,现在恐怕只有我一个将就着用了。所以,您现在说的实在有些强人所难了,您在这行业做了这样久,也算是行家了,自然懂得此中道理。”
顾明晨手里抓住了一只空心玻璃杯,不知不觉用了些力,忽然听到“啪啦”一声,只见内层的玻璃竟然碎裂了,他扔掉杯子,轻轻抽了一张纸巾,抹去了涌出来的血迹。他抬头看到,对面的女人仍旧用淡漠的眼神看着自己,心头蓦地被刺了一下。从来在谈判桌上自己都是主导,但是此刻在这女人面前,他觉得这状况似乎有些失控。
于是,他轻咳一声,说:“我们公司和你们岁月流光艺术发展有限公司是签过长期合作合同的,这合同是有法律效力的,履行合同是你们公司的义务,现在无论你找多少理由,还是要履约的。”
黄欣悦眯着眼皮,回答:“我本来是个公私分明的人,不想在工作中涉及个人隐私,但现在顾总既然不肯通融,那我也只好自报家门了。从这画的装裱风格上看,是出自我的表姨父任文良之手,他虽然只是美术老师出身,但是曾经得到过民间艺术大师的教授,多年对裱画深有研究,在古画裱画界也算是一个资深的元老了。所以我想回去询问一下,这画真假自辩。请问顾总,这样的解释您满意了?”
“任文良?”顾明晨虽然没有听说过这个名字,但他知道民间有很多业界高手,暂且不论这《疏林寒绿图》是真是假,也不论其绘画功力如何高深莫测,他看的出来,仅凭这裱画的技艺就实在是超凡脱俗,自成一派。他沉思了片刻,说:“怪不得……那好,就给你一周时间,然后一定要有个说法,否则我不但中止合同,还要索赔!”
黄欣悦不满地看了一眼顾明晨,暗道这商人的嘴脸真是变化无常,她点头说:“好,那顾总我出去了。”
顾明晨挥挥手,瞪着她开门离开,这才气鼓鼓地喝了一杯咖啡。他低头看到桌子上那幅画,不禁有些觉得奇怪,又将它打开细细窥视一番。那画里的水木皆生动逼真,即便是孤寂,也不知不觉充满了一种向上的力量,这力量到底出自哪里?他又看了看盛懋的资料,其人在当朝并不算上顶级大师,但他的作品吸取了宋元两代山水画的特点,贴近自然,笔墨图式复杂多样,不可小觑,古画界对其流传于世的作品也颇有微词,但是正是这种不同,反倒提升了其内在的价值。这《疏林寒绿图》也确实符合他素常的书画作风,但是确实没有人可确定他到底是不是盛懋亲笔。
顾明晨用手指敲着桌面,不小心触动了刚才的伤口,他看了看自己的手指,又渗出一丝血迹,不由苦笑一声。对于拍卖行来说,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他不敢肯定,这个貌不惊人的女人,真的可以撑起这一切。但是目前也没有特别好的办法,他按捺住内心的浮躁,不得不把所有的一切都压在这个女国画修复师身上。他暗暗捶了几下有些发紧的额头,眼睁睁看着她的身影渐渐消失。
黄欣悦没有再见任婷,因为她要去的地方,是任婷最不想回去的家,她怕稍有不慎会触动任婷内心的底线,于是独自悄悄出了文道拍卖行的大门。外边的风还是有些清冷,她捂着脸深深呼吸了一口。没有人知道,她是怎样拼命抑制自己内心的翻涌,她怎么敢相信,姨父所用的裱画纸张居然是传说中的白鹿纸?小时候和任婷、任鹏追逐打闹,偷偷翻遍姨父的书柜,从来没有看到过这种纸张,她不敢相信自己的判断,不敢相信姨父会为了一幅假画费尽心力装裱,这是藏在她心头难以述说的东西,所以她觉得一刻都不能迟缓,要早些见到姨父。
手机忽然响了起来,是任婷。黄欣悦犹豫了片刻,还是按下了键。
“黄欣悦,你也不打个招呼就离开了,我这话还没说完呢!记住啊,不许告诉家里我在这里上班,如果我知道是你说的,我一定跟你没完!”
黄欣悦想了想,说:“好,我答应你。如果我说了,你可以和小时候一样用脸盆泼我一头脏水!”
对方传来“哼”的一声,然后就挂断了,只听到滴答滴答的忙音。
她从来都记得很清楚,那是初冬一次大雪后,她的语文考了全班第一名,当她兴冲冲地抱着奖状回家,刚打开门,忽然觉得头上被什么东西撞了一下,瞬间一脸冰冷的臭水灌入了脖颈里。她看到一只破旧的牡丹花搪瓷盆扣在地上,散发着恶臭的味道。她打了一个冷颤,看到任鹏嬉皮笑脸地跳了出来,趁她不注意一把夺过她手中的奖状,喊着:“姐姐,怎么样?我说她肯定中招,哈哈,还拿着奖状想讨好爸妈呢?”
黄欣悦看到任婷拿着一把木梳,梳着自己的一头长发,皱眉说:“还拿着奖状想回家显摆?不过,让你失望了,我爸妈今天出门看望老朋友去了,不在家,你这张破纸就没人看了。”她忽然得意地笑了笑,几下就将那奖状撕了几把,往地上一扔,然后扬长而去。
任鹏又蹦跳着,朝黄欣悦挤着鬼脸:“我看你这回找谁哭诉?我看你没事老是逞能?你可臭死了,赶紧离我们远点!”
黄欣悦浑身透凉,她看到任鹏与任婷的脸压在窗户玻璃上偷偷笑着,自己的奖状被撕得到处飞扬,泪水蓦地流出来,于是她迎着不时袭来的寒风,追着将那些纸屑都捡了起来。
天色渐渐暗黑,屋外被雪映衬得如同白昼,任文良与刘淑惠还没有回来,她只好自己把衣服换了、洗了,然后到了任文良的裱画室里。那里还摆放着任文良早上用过的半瓶浆糊。曾经有无数次,她看到姨父就是这样带着围裙,将一大团面揉合,然后醒上个把钟头,放水洗去面筋,再添加上自己独特的草药配方,熬成可以装裱用的浆糊。
她找了一张被任文良废弃的白纸,将奖状的碎片一一拼接起来。想着姨父平常说的话:“可别小看这两把刷子,千古流传的手艺都在这里。”她学着姨父的样子,将那些碎片用浆糊一一粘贴,但是中间少了一块,就是缺少写着黄欣悦名字的那一块。黄欣悦抹了几把眼泪,在姨父废弃的碎纸里找了一块和奖状硬度差不多的纸,剪成和破洞差不多大小的面积,开始贴补起来。但是那纸张的颜色还是相差了很多,黄欣悦的小脸哭得有些皴了,摸上去还有些微微疼痛。但是,她只是想将它拼好,她只想要一张完整的奖状。
她拿起衣姨父的毛笔,用些红色的颜料将那块补洞的纸轻轻描上颜色,还学着用毛笔写着自己的名字,但是她无论如何也驾驭不了那支笔,于是她一边哭,一边继续描着……就这样,她不知不觉睡着了。等她醒来,就已经睡在自己的床上了。
她的意识是模糊的,感觉自己唇齿间还残留着药物的苦味,忽然听到姨父训斥任婷与任鹏的声音:“怎么回事?姐姐病了你们两个怎么无动于衷?我平时是怎么教你们的?”
她还听到表姨的声音:“孩子们还小呢,自己能把自己照顾好就不容易了,现在欣悦这不就是个感冒发烧,过几天就好了,不要成天和凶神恶煞似的,孩子们都和你不亲了。”
“哼,都是你给惯的。”
黄欣悦感到一双非常粗糙的大手在自己头上摸了摸,说:“这药还真是管用,欣悦,好好睡一觉,明天就好了。”
她很想和姨父说句话,但是什么都说不出来,意识又模糊了。
再次醒来,她觉得自己的头清醒了很多。她看着四周,到处静悄悄的,忽然看到桌子上有一盘芝**仁点心,下边还压着一张纸。那张纸飘落下来,她捡起来,原来是自己那张奖状,最令人惊奇的是,这张奖状完整如昔,竟然看不出一丝一毫曾经破碎过的痕迹。
她不敢置信地揉了揉眼睛,确实是写着“黄欣悦”同学名字的那张奖状,“黄欣悦”那三个字与其他的字浑然一体,根本看不出来是修补过的。
她知道这一定是姨父亲自修复的,但是这种神奇的技艺,从此就在黄欣悦幼小的心灵留下了深深的痕迹。
午后的阳光是一天中最暖的了。黄欣悦站在通往表姨家的胡同口,这条胡同很深,与正街相通,胡同口放着一辆破旧生满了锈、只有一只轮子的老自行车,园艺工人没有将它清理出去,而是借物造景,将它给那些藤本蔷薇做了支撑。一株有些年岁的国槐在阳光下拉出了长长的影子,那稀疏的枝干隐隐露出几分绿意。黄欣悦帮着往胡同里边骑去的快递三轮,捡了一件掉落的快件,快递小哥连连说了几声“谢谢”,让黄欣悦有些羞怯起来。
表姨家在胡同的尽头,那扇门似乎刚刚刷了一层新漆,黄欣悦犹豫了片刻,还是推开了那扇门。她的童年,是过去时光里难以述说的一段存在。她三岁那年,父亲忽然死去,母亲将她带到这里,从此这里就盛满了她童年全部的记忆。表妹任婷、表弟任鹏后来接连出生,这个家就是在表姨刘淑惠的抱怨声、表姨父任文良的叹气声中流淌着日子的琐碎。
虽然这些年她不知道母亲去了哪里,母亲为什么就她寄放在这里一去不返,但是她察觉的出来,表姨父是一直护佑着自己的,并没有苛待自己,反而比对自己的亲生子女还要好。他曾经为黄欣悦凑够了攻读研究生的生活费与学费,不惜日夜赶工,将自己的手给折腾肿了许多天才痊愈。而和她有着血缘关系的表姨刘淑惠却对她不冷不热,她只是一味溺爱着自己的两个孩子,因此任鹏高考落榜后,就再也没有复读。他后来在一家房地产公司做保安,本来也能过上安生日子,但是他却始终没有让父母省下心,打架酗酒折腾了几次,被公司辞退,只好终日游荡闲赋。
黄欣悦想着,迈开步子朝里走着。院子里很安静,也收拾得非常利落。东南角是一大簇黄槽竹,这是北京庭院里最常见的竹子品种,自从表姨家住在这里以来,便一直都长得很旺势,春光明媚的日子里,这片竹影斑驳,浓淡相宜,也因为有了它们,无形中给庭院增添了一抹生机。一张老榆木桌子,几把老竹藤椅子是平常家人一起在庭院里吃饭用的,也都看不到什么灰尘。表姨刘淑惠似乎不在家。她看了看正屋墙壁上的一只老雕花木的钟表,这个时辰应该是表姨出去买菜的时间,估计也快回来了。
她的脚步很轻,不敢发出声音。每当这个时辰,是姨父潜心工作的时刻,她站在窗口,看到姨父任文良身上围着围裙,手中拿着一把大刷子,正专心地在一张三尺多长的纸上用力刷着。
黄欣悦很熟悉这道工序,这道工序叫托复背。就是要给裱好的画上再一层或多层的纸。这纸不能太薄,也不能太厚。不可以用熟纸、绢帛、毛边或者报纸来代替,否则日久易破,也会有损原作。但见眼前一位鬓角早生华发的老人,正扬起一张棉连纸,仔细覆盖在画上,然后熟练地刷上浆糊,然后又扯出一张纸,覆盖在上边,再继续刷下去……阳光中,瘦削的身影与扬起的纸张融为一体,整个看起来便是人与纸的美妙共舞。
黄欣悦看到姨父将做好的复背纸,轻轻刷在一张书画作品上,方才轻轻舒了一口气。看到这里,黄欣悦进门,轻轻喊了一声:“姨父。”
“欣悦,你回来了?”任文良看到黄欣悦进门,紧绷的脸上骤然舒缓了许多,看的出很开心,他笑着说:“赶紧,帮我一下。”
黄欣悦点头,和过去一样,帮助表姨父小心翼翼扶住那画,慢慢讲那画贴到墙上。
任文良又拿出那把鬃刷,屏住了呼吸,顺着纸张的纤维方向轻轻地刷了过去,在覆背纸四边抹上浆糊,最后将复背纸与画固定在墙壁上,才终于完全放松下来。此刻,墙壁上的画带着特殊的药香与未曾干涸的浆糊味道,险些将黄欣悦的眼泪勾了出来。
耳边听到任文良如获重视般地又舒了一口气:“现在天气越来越暖和了,我这心里就踏实了,不怕它给崩了,到时候没法交代。”
黄欣悦轻轻吸了一下鼻子,说:“姨父,您裱了这么多年的画,真是万物一失吗?真的没有出过差错?”
任文良“哼”了一声:“我也不是大罗金仙,怎么可能没有出过差错?当年……”
黄欣悦正想继续听下起,忽然听到任文良顿了一下,似乎想起了什么,不再往下说了。
这是许多年来黄欣悦最习惯的场景了,表姨父本来就是个话不多人,只是偶而心血来潮,才会坐下来喝几杯酒,每次都是表姨陪着他喝,表姨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文良,你有什么话不要闷在肚子里,不如和我说一说。”任文良总是应一句:“老夫老妻了,都半辈子了,还说个啥呀!”说到这里便睡过去了,只留下表姨一个人说:“还说什么老夫老妻,就是半辈子了又能怎么样?我只是想听你一句真话,我过分吗?可惜了,我这头发都白了,也等不着,看来是我从上辈子就欠了你吧!”
每当想起小时候这些场景,成年的黄欣悦似乎明白了些什么。表姨这辈子心里只有表姨父一个人,但是,表姨父的心思难以捉摸,也似乎在他默默劳作的漫长岁月里,还曾经有过一段旖旎的回忆,但是,黄欣悦还没有想透,那到底是什么。
她听母亲说过,表姨与表姨父这门亲事,是自己的外祖父颜祖山亲自做的媒,表姨是外祖母亲妹妹家最小的一个女娃,生的漂亮大气,于是便托付外祖父将她嫁给了自己的二弟子任文良,表姨父之前在中学教书,表姨就在学校的食堂里工作,现在退休后,更是一心意打理家事。
正想着,听到门忽然开了,刘淑惠提着一只老母鸡回来,那只鸡的腿和翅膀都被白布带绑着,还试图挣扎着,听到她一边走一边骂:“你这是贼心不死呀!都死到临头了,还折腾什么,认命就是了。”
黄欣悦站直了身子,朝刘淑惠喊了一声:“姨。”
刘淑惠怔了一下,似乎有些吃惊,但是很快就镇定如常了:“回来了?怎么也不提前打个电话说一声?”
任文良看着那幅画,点了点头,说:“这是她自己的家,想什么时候回就什么时候回,打什么电话?这不,还是她姨有先见,连老母鸡都买回来了,赶紧收拾一下,炖一锅红烧鸡炖土豆,欣悦最爱吃这口了。”
刘淑惠的表情僵了一下,低声说:“你不是总说自己的手脚有些不利落吗?我是听说用天麻炖老母鸡可以治你这毛病,所以……”
任文良大手一挥,将腰上的围裙摘了下来,喝了一杯桌子山早已经放凉了的菊花茶,“嘿嘿”一笑,不以为然地说:“别提那些捕风捉影的话,要是真吃了只老母鸡,人就利落了,那些大医院不早就关门了?”
黄欣悦忧心忡忡地看了任文良一眼,只见他不停地捋着自己的食指,问:“姨父,您的手?”
任文良“哈哈”一笑,说:“没什么,就是觉得近日有些发麻,我天天干的是这个裱画的精细活,这手指头想坏了都没那种可能。”
刘淑惠“哼”了一声:“看你逞能的!要不是看你成天辗转反侧,半夜老起来捶腿搓手的,我才不可怜你呢!”
“别说了,赶紧烧壶开水,烫了拔毛,好不容易孩子回来的,听说我,别放那什么天麻,炖土豆。”
黄欣悦连忙摆手:“不,姨父,我现在在外边工作,最注重形象了,不敢吃太多,这个老母鸡油太大,我可不敢吃,我有些蔬菜就可以了。”
任文良瞪眼:“什么?怎么这口气和任婷似的?可千万别学她,光想着什么减肥漂亮什么的,成天描眉画眼的,穿着都是什么奇装异服呀?每次一回胡同,别人都当怪物一样看着她,她怎么也不知道寒掺呢?”
黄欣悦听到又把任婷给扯出来了,表姨刘淑惠的脸色有些怪异,连忙打断了任文良的话:“我来做吧!”
任文良摇头:“淑惠,你去做饭,欣悦的手现在也是做精细活的,不要让她做这些琐碎的家务事了,你就代劳吧!听我的,炖土豆。来,欣悦,到里屋去,我有话对你说。”
任文良的书房是院子里的西耳房,最大的一间厢房是他的工作室,其他的是三个孩子的屋子,所以只剩下这一间耳房可以当书房了。此刻,大概是下午四点多了,光线已经有些昏暗了。任文良的书桌上摆放着一幅破旧的古画。
他一边摸了摸膝盖,一边坐了下来,说:“欣悦,我知道你回来肯定是有事要问我,有什么事就说吧,不要吞吞吐吐的。”
黄欣悦的鼻腔里忽然涌出一股酸楚的味道,她轻轻吸了一口气,说:“姨父,我见到了一幅画,那幅画的味道好熟悉。”
“什么画?是画得味道还是装裱的味道熟悉呀?”任文良一边问一边拿着放大镜看着那幅画中间破的一个洞,似乎在深深思考,下边的工序应该怎么做,才能将它完好无缺的补上。
黄欣悦闭了下眼又睁开,鼓起勇气说:“您常常说,这好画是三分画七分裱,但是我看到的这幅画不仅仅从裱功上看登峰造极,那画工也是非同小可,还有最奇怪的是,那张裱画用的纸,我从来见过。”
听到这里,任文良“哦”了一声,抬起眼皮看了看黄欣悦窘迫的表情:“孩子,你想说什么?”
“我”,黄欣悦鼓足了勇气,终于说出了自己心里的疑问,“我不懂,姨父您为什么会违背初衷,是什么力量让您会耗尽心力裱一幅赝品?”
任文良的神情凝重起来:“你说什么?”
“对,那幅画是元代盛懋的《疏林寒绿图》,这画工确实是盛懋擅长的笔法,但是如果我没有猜错,我母亲当年托付给您的就是这幅《疏林寒绿图》,我真的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如果这画是赝品,那么这画又是谁画的?如果是真品,那……”
黄欣悦很想质问任文良为什么会将母亲的画流失出去?但她看着任文良放下手里的放大镜,皱纹波动,表情凝重,扶着自己的官帽椅,缓缓地坐了下去,只好抿了抿嘴,不敢再说下去。
只见任文良的眼神浑浊迷离,他看着窗口,似乎陷入了难以名状的沉思中,良久,他叹了口气:“孩子,你是在责怪我吗?”
“不,姨父,我感激您对我的养育之恩,我并没有责怪您的意思,我只是想知道真相。”
“真相?”任文良的嘴角微微咧开,那笑容非常复杂深邃,“孩子,你长大了,我也该对你有个交代了。你说得不错,当年你母亲把你和那幅画托付给我,并告诉我,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可以将那幅画变卖,以解燃眉之急。”
“那,您遇到了什么样的燃眉之急?”黄欣悦没有想到自己这话就这样轻而易举地从嘴边溜了出来。
 收藏
收藏  打赏
打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