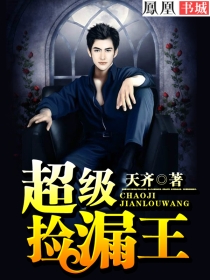正文:第二章 廷真之死
江建龙生有五子,按房份大小,分别居住在东西的厢房中。
在东厢的一间房,江廷光正在灯下忙碌。他拿起几根麻绳在来回端看,这些麻绳上都打满活结,每一个结都是他的一笔账,账目明晰的,他会逐个把绳结解开。
“他戴孝在身,晦气那么重,真不应该过来串门!”江李氏的嘴巴,仍在喋喋不休。
“你少说两句。等天放晴后,你拿这几根麻绳出去晒一晒。”
“哪里是晒麻绳,分明是晒你的账本。”
江李氏从床上探出脑袋,她身旁的两个孩子早已在被窝中恬然酣睡。房中,除却她这一阵咯咯的浪笑,到处静得唯有夜雨的呼吸声。
江廷光长得眉清目秀,但他是一个目不识丁的鱼贩。自十五岁起,他常年跟随父亲,按一四七、二五八、三六九的各镇圩日,在桐地一带的地区上东奔西走。
“生气了?”江李氏问道。
“我正忙着。”
“你看,阿爸多有文化。你整天却捣鼓麻绳,跟闹上吊似的。”江李氏推开被子,捧腹大笑。
从东厢迂回过天井,再穿过堂屋与廊道,是西厢。
新婚燕尔的江廷源,正翘起二郎腿躺在床上。青春从他黝黑的肤色中喷涌出来,在崭新的大红被面上长流不息。
江廷源比江廷光年少十岁,是江家最小的儿子。他长得五大三粗,相貌彪悍。在成年后,他主动追随父兄的脚步,外出做生意。
“雨越下越大了?”
“没有。”
灯光已落地生花,双眸含羞的江王氏,笑靥如花地从其间款款而过。江廷源不时地抬眼与她对视,可是更深情的言语始终没能滑出嘴皮,只能任由雨水在屋背上缠绵悱恻,雨落声清脆而绵长。
“不会吧?”
“真的。”
“你听!屋背上好响!”江廷源跳起来。
“是猫!它在屋梁上赶老鼠。”
“真气人,明天又要早起。”
“不正经!我知道你在想什么!”江王氏抬眼看他,忍不住嫣然一笑。
大宅院中,忽然响起几声狗叫。江建龙把胡中扬送到门外,继续给他说一些宽心的话。等胡中扬慢慢地走远,他才把重重的大门重新关起来。
“来人啊!廷真不行了!”
忽然,东厢这一边呼声大作。
体态修长的江黄氏,从房中冒冒失失地扑出来,她边跑边喊,慌乱异常。刚满周岁的儿子江声,正蜷缩在她的胸前,若无其事地吃奶。
两扇厚重的房门,在喊声中同时旋转起来,为她倩丽的身影,划出一道美丽的弧线。
江廷光赶紧丢下手中的麻绳,率先冲进江廷真的房中。他看见江廷真已经瘫倒在床前,如同一片秋叶,在满地的蜡黄中找不出一丝生机。
“怎么回事?他刚才还好好的!”
江黄氏哭道:“吃完晚饭,他一直喊胸口疼。”
“他可能是犯心病!廷源,你快去找医生!”
江廷光赶紧回头,大喊一声。
这时,江廷汉、江廷奎和江廷源三人,全部都已赶到房中。江廷源闻声,马上忍住泪水转身夺门而去。房中的其他人一起动手,把江廷真抱到床上。
随后快步赶来的江建龙,脸上依旧镇静自如。他深吸一口气,拿起江廷真的手腕,在脉搏上摸索起来。
“廷真——”
江建龙突然大喊一声,悲恸难支。
在江廷真死后,江建龙大病一场,一连三天都无法迈出房门。每当夜晚来临,他的房中总是传出一阵抑扬顿挫的诗句。江周氏一个人静静地端坐在堂屋的木椅上,聆听这些悲伤,她任由泪珠,时而滑过自己那一张美丽如故的脸庞。
“是胡中扬害死了廷真,他一定不得好死!明知自己正在戴孝,还故意过来串门!”
江李氏每天带领三房与四房的女人,一起跑到大宅院的门前,泪流满面地咧咧而骂。
泪落之声真的很好听,只是很悲伤,一声声地响彻民国的天空。
到初冬的一天,大病初愈的江建龙,终于推门而出,走到村前的田埂上。
他眼中的这一片土地,每到春夏间,在山包与河堤上都会开满鲜花。清风吹至,连老水牛都会惬意地眯上眼睛。
只要到秋日,清晨在黄熟的稻穗上,蒙着一层薄霜,太阳出来晶莹剔透。在傍晚,成群的麻雀在稻田里欢快起舞,而醉红的夕阳在牛背和树梢上远走。
到深冬,在桐地的瓦舍两旁都会堆起高大的草垛。天空飘起牛毛雨,雨水沿着稻草一直往下滑落。那时,山野上的荒草都已枯黄。北风像喝多一样,一路微笑而来,沿山边和屋脊进村寻找。
一阵北风吹过来,历历的往日景象让江建龙慢慢地闭上双眼,再深深地呼吸一口空气。他知道,天幕之下,总有延绵的炊烟和忧伤,总有雄浑的岁月和生老病死。
“阿爸,外面风大,你回去吧。”
身边突然传来一个声音,江建龙睁开眼睛,他看见江廷汉急匆匆地从田里赶过来。
“不怕。你还记得吗,今天是你二哥的生日。”
“我记得。”
“廷真的死,令我心痛啊!我们江家读书的种子,说没就没了!”
江建龙重重地叹出一口气,浑浊的老泪,从脸上滴滴滑落。
“阿爸,如今的世道不太平,你要保重身体,撑住这个家啊。至于以后的事情,你别想太多,儿孙自有儿孙福。”
“你的眼里除了一亩三分地,还有什么!耕作是为生存,读书才能继世!”
江建龙拂袖而去,在他远去的背影中,冬日的田野如同飞鸟过后的天空,除了风什么都没有。
“读书,读书!那你干嘛跑去卖咸鱼?”
江廷汉嘀咕一句,扭头朝田野的深处走去。
江廷真的墓地座落在北面的山中,山上有一片树林,山下有一道水。一堆黄土在苍鹰的翱翔与鸣叫中,显得萧然凄楚。在他出山那天,江建龙在他的墓前烧掉一捆书。山风吹至,纸灰盘旋起来,如同苍鹰一样飞舞。
从田埂上回来,江建龙还在一边走一边想,在他的泪眼过处,满地都是叹息。
“二叔,我对不起你!”
胡中扬忽然在村道上拦住江建龙,他双膝跪地,泪如雨下。
“中扬,你快起来。”
“不,我真的是错了!我不该听从道士的话,害死廷真。”
“他说什么?”
胡中扬泣不成声地道:“他叫我在戴孝期间,去找一户人家串门,这样才能破除我们家族的诅咒。”
“你!”
江建龙一手抓住他的衣领,把他提起来。
“二叔,我糊涂啊!”
江建龙抬脚把他踹倒在地上,冷冷地道:“生老病死,都是命中注定。你和道士又有何德何能,可以大言不惭地害死廷真?我告诉你,你今天的这一番话,就让它烂在肚子里,今后别再提起。”
冬天的夜,来得特别早。山风还没有收回它在白日间的流浪,夜幕早已把天地盖得严严密密。
江廷汉收工回来,他顾不上吃晚饭,径直跑进江建龙的房中。
江建龙抬头道:“廷汉,你回来了。”
“阿爸,怪事!我刚才在收工回来的路上,无意中看见有一支几十人的队伍,他们扛着刀枪从我们的村边走过。”
“是兵,还是贼?”
“天色已晚,我没有看清。”
“田里的庄稼都收完没有?现在,时近岁末,各地的山贼肯定又会猖狂起来。你赶紧去把廷光叫过来,我让他明天去多买几把长刀回家,提防山贼进村打家劫舍。”
“我听说,林苗镇有一条村在前几天被抢了。村民去官府里报案,到现在都没人来处理。”
“你记住,每个人都只是大地的一根胸毛,在盛世当忍,在乱世当强。千万不要把宝压在别人的身上,就连是政府,也是徒劳。去吧,快把廷光叫过来。”
江廷汉似懂非懂地点点头,推门而去。
桐地的夜,又重重地厚了一层。
在东厢的一间房,江廷光正在灯下忙碌。他拿起几根麻绳在来回端看,这些麻绳上都打满活结,每一个结都是他的一笔账,账目明晰的,他会逐个把绳结解开。
“他戴孝在身,晦气那么重,真不应该过来串门!”江李氏的嘴巴,仍在喋喋不休。
“你少说两句。等天放晴后,你拿这几根麻绳出去晒一晒。”
“哪里是晒麻绳,分明是晒你的账本。”
江李氏从床上探出脑袋,她身旁的两个孩子早已在被窝中恬然酣睡。房中,除却她这一阵咯咯的浪笑,到处静得唯有夜雨的呼吸声。
江廷光长得眉清目秀,但他是一个目不识丁的鱼贩。自十五岁起,他常年跟随父亲,按一四七、二五八、三六九的各镇圩日,在桐地一带的地区上东奔西走。
“生气了?”江李氏问道。
“我正忙着。”
“你看,阿爸多有文化。你整天却捣鼓麻绳,跟闹上吊似的。”江李氏推开被子,捧腹大笑。
从东厢迂回过天井,再穿过堂屋与廊道,是西厢。
新婚燕尔的江廷源,正翘起二郎腿躺在床上。青春从他黝黑的肤色中喷涌出来,在崭新的大红被面上长流不息。
江廷源比江廷光年少十岁,是江家最小的儿子。他长得五大三粗,相貌彪悍。在成年后,他主动追随父兄的脚步,外出做生意。
“雨越下越大了?”
“没有。”
灯光已落地生花,双眸含羞的江王氏,笑靥如花地从其间款款而过。江廷源不时地抬眼与她对视,可是更深情的言语始终没能滑出嘴皮,只能任由雨水在屋背上缠绵悱恻,雨落声清脆而绵长。
“不会吧?”
“真的。”
“你听!屋背上好响!”江廷源跳起来。
“是猫!它在屋梁上赶老鼠。”
“真气人,明天又要早起。”
“不正经!我知道你在想什么!”江王氏抬眼看他,忍不住嫣然一笑。
大宅院中,忽然响起几声狗叫。江建龙把胡中扬送到门外,继续给他说一些宽心的话。等胡中扬慢慢地走远,他才把重重的大门重新关起来。
“来人啊!廷真不行了!”
忽然,东厢这一边呼声大作。
体态修长的江黄氏,从房中冒冒失失地扑出来,她边跑边喊,慌乱异常。刚满周岁的儿子江声,正蜷缩在她的胸前,若无其事地吃奶。
两扇厚重的房门,在喊声中同时旋转起来,为她倩丽的身影,划出一道美丽的弧线。
江廷光赶紧丢下手中的麻绳,率先冲进江廷真的房中。他看见江廷真已经瘫倒在床前,如同一片秋叶,在满地的蜡黄中找不出一丝生机。
“怎么回事?他刚才还好好的!”
江黄氏哭道:“吃完晚饭,他一直喊胸口疼。”
“他可能是犯心病!廷源,你快去找医生!”
江廷光赶紧回头,大喊一声。
这时,江廷汉、江廷奎和江廷源三人,全部都已赶到房中。江廷源闻声,马上忍住泪水转身夺门而去。房中的其他人一起动手,把江廷真抱到床上。
随后快步赶来的江建龙,脸上依旧镇静自如。他深吸一口气,拿起江廷真的手腕,在脉搏上摸索起来。
“廷真——”
江建龙突然大喊一声,悲恸难支。
在江廷真死后,江建龙大病一场,一连三天都无法迈出房门。每当夜晚来临,他的房中总是传出一阵抑扬顿挫的诗句。江周氏一个人静静地端坐在堂屋的木椅上,聆听这些悲伤,她任由泪珠,时而滑过自己那一张美丽如故的脸庞。
“是胡中扬害死了廷真,他一定不得好死!明知自己正在戴孝,还故意过来串门!”
江李氏每天带领三房与四房的女人,一起跑到大宅院的门前,泪流满面地咧咧而骂。
泪落之声真的很好听,只是很悲伤,一声声地响彻民国的天空。
到初冬的一天,大病初愈的江建龙,终于推门而出,走到村前的田埂上。
他眼中的这一片土地,每到春夏间,在山包与河堤上都会开满鲜花。清风吹至,连老水牛都会惬意地眯上眼睛。
只要到秋日,清晨在黄熟的稻穗上,蒙着一层薄霜,太阳出来晶莹剔透。在傍晚,成群的麻雀在稻田里欢快起舞,而醉红的夕阳在牛背和树梢上远走。
到深冬,在桐地的瓦舍两旁都会堆起高大的草垛。天空飘起牛毛雨,雨水沿着稻草一直往下滑落。那时,山野上的荒草都已枯黄。北风像喝多一样,一路微笑而来,沿山边和屋脊进村寻找。
一阵北风吹过来,历历的往日景象让江建龙慢慢地闭上双眼,再深深地呼吸一口空气。他知道,天幕之下,总有延绵的炊烟和忧伤,总有雄浑的岁月和生老病死。
“阿爸,外面风大,你回去吧。”
身边突然传来一个声音,江建龙睁开眼睛,他看见江廷汉急匆匆地从田里赶过来。
“不怕。你还记得吗,今天是你二哥的生日。”
“我记得。”
“廷真的死,令我心痛啊!我们江家读书的种子,说没就没了!”
江建龙重重地叹出一口气,浑浊的老泪,从脸上滴滴滑落。
“阿爸,如今的世道不太平,你要保重身体,撑住这个家啊。至于以后的事情,你别想太多,儿孙自有儿孙福。”
“你的眼里除了一亩三分地,还有什么!耕作是为生存,读书才能继世!”
江建龙拂袖而去,在他远去的背影中,冬日的田野如同飞鸟过后的天空,除了风什么都没有。
“读书,读书!那你干嘛跑去卖咸鱼?”
江廷汉嘀咕一句,扭头朝田野的深处走去。
江廷真的墓地座落在北面的山中,山上有一片树林,山下有一道水。一堆黄土在苍鹰的翱翔与鸣叫中,显得萧然凄楚。在他出山那天,江建龙在他的墓前烧掉一捆书。山风吹至,纸灰盘旋起来,如同苍鹰一样飞舞。
从田埂上回来,江建龙还在一边走一边想,在他的泪眼过处,满地都是叹息。
“二叔,我对不起你!”
胡中扬忽然在村道上拦住江建龙,他双膝跪地,泪如雨下。
“中扬,你快起来。”
“不,我真的是错了!我不该听从道士的话,害死廷真。”
“他说什么?”
胡中扬泣不成声地道:“他叫我在戴孝期间,去找一户人家串门,这样才能破除我们家族的诅咒。”
“你!”
江建龙一手抓住他的衣领,把他提起来。
“二叔,我糊涂啊!”
江建龙抬脚把他踹倒在地上,冷冷地道:“生老病死,都是命中注定。你和道士又有何德何能,可以大言不惭地害死廷真?我告诉你,你今天的这一番话,就让它烂在肚子里,今后别再提起。”
冬天的夜,来得特别早。山风还没有收回它在白日间的流浪,夜幕早已把天地盖得严严密密。
江廷汉收工回来,他顾不上吃晚饭,径直跑进江建龙的房中。
江建龙抬头道:“廷汉,你回来了。”
“阿爸,怪事!我刚才在收工回来的路上,无意中看见有一支几十人的队伍,他们扛着刀枪从我们的村边走过。”
“是兵,还是贼?”
“天色已晚,我没有看清。”
“田里的庄稼都收完没有?现在,时近岁末,各地的山贼肯定又会猖狂起来。你赶紧去把廷光叫过来,我让他明天去多买几把长刀回家,提防山贼进村打家劫舍。”
“我听说,林苗镇有一条村在前几天被抢了。村民去官府里报案,到现在都没人来处理。”
“你记住,每个人都只是大地的一根胸毛,在盛世当忍,在乱世当强。千万不要把宝压在别人的身上,就连是政府,也是徒劳。去吧,快把廷光叫过来。”
江廷汉似懂非懂地点点头,推门而去。
桐地的夜,又重重地厚了一层。
 收藏
收藏  打赏
打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