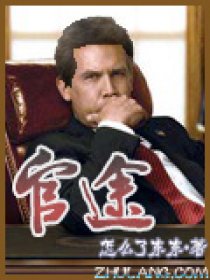正文:六、老聂
他们到老聂家时,家中没人,房门大开着,空空荡荡。
山里的村子不象山外的,只有十几户人家,每户的屋子都比较小,而且零零落落。老聂家与其他的农户隔了有好远,孤零零地。一间正房,依着地势盖的,不当不正。盖房的材料多是石头,一个半人高的棚子,装柴火和杂物什么的。
刘大松赵腊梅查看了一下,炕上没被子,但席上没有特别多的尘土,缸里有一多半水,灶里的柴灰看上去比较新,锅上的积渍是软的,这屋是有人住的。
老聂是不在家,还是不明情况躲出去了?找吧,真不知应该到哪去找,还是等吧。
刘大松与赵腊梅商量,就先休息一下,如果等不到,然后半夜起身再往山里走。
大家利用老聂家的水和柴火,点火热干粮,烧开水。
刘大松挑着水桶找到附近一户人家,敲开门,问水井在哪里。
开门的是位老大爷,一见八路来了,一时激动的不得了。
刘大松说,自己只是过路的,半夜就走。问水井,是因为用了老聂家的水,要还上人家。明天鬼子可能要来,要是问我们去哪里了,就照直说,往山里边去了。
大爷一听刘大松是独自过路,有些失望。没有多说话,指了水井的位置。
刘大松挑水回来,就觉得后边有人跟着,他放下水桶,转身看去,不远处站着一人。
他就是老聂。进到屋里,借助火光,刘大松看出个大模样。老聂完全是个老农的样子,一丁点看不出当过兵、做过大领导的样子。刘大松有些失望,有些担心。
赵腊梅先介绍了自己,只说了以前的职务,没提已经被精简的事。然后细细地说了今天发生的事情,虽然一整天里发生了那么多事,但赵腊梅说的繁简得当,清清楚楚。完了之后,又谈了自己的打算,希望老聂能出来挑这个头。
老聂一直在注意的听,不动声色,问了一些细枝小节,然后拿过那把短枪,抽出枪来,翻转过来看了看。然后说道,你的计划也许能行。
老聂说了自己的想法。这一带变成敌占区已经有些日子啦,区政府只有几个警卫员。一次干掉伪军一个班,很久没有这样的事了。鬼子一定要派兵到处搜你们,但能不能找到这里,还不好说。咱们这里不同就是这个沟,顶头的山那边都是悬崖峭壁。这么多年,从没有队伍往这山里钻过。
刘大松问,要是二狗子进来搜呢?
老聂说,看人多人少啦。咱们打呢,不能依托村子,必须到山上去。这山大,路险,沟沟坎坎多,人容易藏。但是呢,山上没什么东西吃,鬼子在山下一住,会被困在上边了。听说路北西崞的同志们,经常被困在山上,十天半个月的在山里转。咱们能不能坚持住,关键要看日伪对咱们的判断,要是重视咱们,他们可以在整条沟来个无人区,把乡亲们往外一赶,在关键的地方设一个炮台,咱们是没办法坚持的。如果他觉得你在这沟里,几个人几条枪,不出来闹事,整条沟里边也就几百口人,都是薄地,产不了多少粮食,没什么油水,就在山门村设个卡,就完事了。至于咱们在里边是死是活,他不管,反正你不会出来闹事。
刘大松问,明天会怎么样呢?
老聂说,什么都有可能,往好处争取吧。小赵说,你的枪法好,一里远的人也能一枪打上?
刘大松说,我这把枪不错,只要能瞄上,就能打上。
老聂说,这样吧,你们先抓紧休息,可能半夜就要出发。我家地窖里还有点吃的,明天一起扛上山,可以多顶两天。我去找个人,半夜前能回来。小赵,有几句话跟你说一下。
领着大家把地窖里的食物取出之后,老聂就匆匆走了。大家在屋里休息,刘大松和赵腊梅两人来到小棚子,扒拉些草秸作铺垫,并肩坐下。
刘大松问,老聂说了什么。
赵腊梅说,问你的事吧。老聂说,要赶快把你送走产。我说,怎么走呀?前山出不云。就是出去了,都是鬼子二铬子。从后山爬悬崖,多危险呀。留下也不错吗,能给我们撑个腰。老聂批评我了,说我有本位主义。
刘大松没听说过这个词,不明白是什么意思。
赵腊梅解释说,就是光考虑自己这方面。
刘大松觉得好玩,地方上的东西真是跟队伍上的有许多不同,我们叫个人主义。
赵腊梅一边比划,一边解释,个人主义小,本位主义大。比方说,你是部队上的,我是地方上的,咱们的工作都是蒸干粮,我这忙不过来,就把你抓来帮忙,结果我的干粮蒸好了,你那灶还没生火呢。
刘大松明白了这帽子是什么色,但没有明白为什么要戴这帽子,老聂批评你这干吗?
赵腊梅说,老聂觉得你是个人才,是我拖累了你。明天要是光藏不打呢,你白跟我们受窝囊气,吃苦受累的不说,还要耽误回部队的时间。要是真刀真枪的干呢,我们只能跑龙套,敲边鼓,这二三十个鬼子二狗子要全靠你一个人顶着。老聂的意思是让我劝你走,回队伍上去。
刘大松说,有一个事情一直不明白,又不好问老聂,咱们为什么不一块走呀?非在这沟里等着人家来呀。赵腊梅说,好走不就早走了吗?东边人家堵着呢。往南往北,要翻山不说,翻来翻去,还是在人家的地盘里。往西呀,那是悬崖,下去了就再也上不来了。山那边是静宁的地盘,不是西忻的。不到万不得已,不能走这一步。
刘大松说,既然这样,我现在就死心塌地跟着你赵干事啦,先打了明天这仗再说。要是能活下来,我再回队伍去。
赵腊梅笑了,这么坚决。
刘大松说,那可不。头一个,我不应该跑,这饼子那来的,老乡从自己嘴里抠出来的,我吃完了,一抹嘴就走,太不地道了。二来呢,这跑了其实也不合算。要是跑的话,我现在就得还山门村走,我到了呢,大概人家也到了,我还得找个地方趴着,让人家先进来。这一折腾,天亮前到咱们自己地盘根本就没门。从芦芽山出来两天多,就在路东的山上眯了那么一下,今天再赶一晚夜路,明天恐怕就算是腿听话,脑袋也不听话啦。要是在哪个草堆睡觉时,叫人家小绳一捆抓了去,那死得多窝囊呀。
刘大松一席话,说得赵腊梅乐哈哈,你呀,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的。就是我笨,不会打枪,要是能跟李林一样就好了。李林是谁你知道吧?
刘大松说,知道,雁北那边的,骑兵营教导员。他们过路南的时候,我接过一次,没看清本人。
赵腊梅叹息道,能文能武的,真可惜的,死的时候还有三个月的身孕呢。你是怎么学会打枪的?我是说,你是怎么能打得这么准?我是不是也能学会?
刘大松说,在段和尚的队伍上没什么象样的训练,我说过吧,我开始不是入的咱们八路军。后来进了三支队,训练的时候,老兵就说我是打枪的料。他们说打枪与赶车有许多相同,主要是眼到手到。再就一眼就能看出有多远,调准标尺。还有眼睛能盯住东西,还有要算风有多大。
赵腊梅听着有趣,你以前是赶大车的?
刘大松说,是啊。这打枪吧,大劲小劲都要有。有人是大劲不够,枪举不稳。有人是小劲不行,搂扳机是两道火,有的人死活搂不出来,扣板机太猛了,枪口就会动。眼睛能盯住东西也是一样,有的人看东西不能看久了,稍微一久就花掉了。
赵腊梅说,我练过画画,能盯住东西,细巧劲我也有,别说两道火,就是八道火我也能搂出来。嗨,我就是没劲,揣不稳枪。要是把枪架好了,我一定能打得准准的。
刘大松说,你可以打重机枪呀。领导说,抢占阵地。大家上去把枪一架,子弹一挂。领导问,怎么不开火呀?这边说啦,报告领导,射手还没有上来呢。领导问,射手干什么去啦?这边说,射手摔了个跟头,把鞋子摔掉了,正满地找哪。
赵腊梅从地上弹了起来,你个死大刘,拿我来开心。说着就朝着刘大松的肩膀上捶了一家伙。
赵腊梅打的并不重,可刘大松却感到全身一颤,一股麻苏苏的劲从上一下子从头顶贯穿到脚底。
再看赵腊梅,她木头一般地呆在那。片刻,她又坐了回去,把头埋在膝盖里,双手紧紧抱着腿,肩膀一抖一颤的。过了半晌,肩膀不颤了,她抬起头,两眼直视前方,平淡的说,你赶快睡吧,一会儿还要站岗呢。
山里的村子不象山外的,只有十几户人家,每户的屋子都比较小,而且零零落落。老聂家与其他的农户隔了有好远,孤零零地。一间正房,依着地势盖的,不当不正。盖房的材料多是石头,一个半人高的棚子,装柴火和杂物什么的。
刘大松赵腊梅查看了一下,炕上没被子,但席上没有特别多的尘土,缸里有一多半水,灶里的柴灰看上去比较新,锅上的积渍是软的,这屋是有人住的。
老聂是不在家,还是不明情况躲出去了?找吧,真不知应该到哪去找,还是等吧。
刘大松与赵腊梅商量,就先休息一下,如果等不到,然后半夜起身再往山里走。
大家利用老聂家的水和柴火,点火热干粮,烧开水。
刘大松挑着水桶找到附近一户人家,敲开门,问水井在哪里。
开门的是位老大爷,一见八路来了,一时激动的不得了。
刘大松说,自己只是过路的,半夜就走。问水井,是因为用了老聂家的水,要还上人家。明天鬼子可能要来,要是问我们去哪里了,就照直说,往山里边去了。
大爷一听刘大松是独自过路,有些失望。没有多说话,指了水井的位置。
刘大松挑水回来,就觉得后边有人跟着,他放下水桶,转身看去,不远处站着一人。
他就是老聂。进到屋里,借助火光,刘大松看出个大模样。老聂完全是个老农的样子,一丁点看不出当过兵、做过大领导的样子。刘大松有些失望,有些担心。
赵腊梅先介绍了自己,只说了以前的职务,没提已经被精简的事。然后细细地说了今天发生的事情,虽然一整天里发生了那么多事,但赵腊梅说的繁简得当,清清楚楚。完了之后,又谈了自己的打算,希望老聂能出来挑这个头。
老聂一直在注意的听,不动声色,问了一些细枝小节,然后拿过那把短枪,抽出枪来,翻转过来看了看。然后说道,你的计划也许能行。
老聂说了自己的想法。这一带变成敌占区已经有些日子啦,区政府只有几个警卫员。一次干掉伪军一个班,很久没有这样的事了。鬼子一定要派兵到处搜你们,但能不能找到这里,还不好说。咱们这里不同就是这个沟,顶头的山那边都是悬崖峭壁。这么多年,从没有队伍往这山里钻过。
刘大松问,要是二狗子进来搜呢?
老聂说,看人多人少啦。咱们打呢,不能依托村子,必须到山上去。这山大,路险,沟沟坎坎多,人容易藏。但是呢,山上没什么东西吃,鬼子在山下一住,会被困在上边了。听说路北西崞的同志们,经常被困在山上,十天半个月的在山里转。咱们能不能坚持住,关键要看日伪对咱们的判断,要是重视咱们,他们可以在整条沟来个无人区,把乡亲们往外一赶,在关键的地方设一个炮台,咱们是没办法坚持的。如果他觉得你在这沟里,几个人几条枪,不出来闹事,整条沟里边也就几百口人,都是薄地,产不了多少粮食,没什么油水,就在山门村设个卡,就完事了。至于咱们在里边是死是活,他不管,反正你不会出来闹事。
刘大松问,明天会怎么样呢?
老聂说,什么都有可能,往好处争取吧。小赵说,你的枪法好,一里远的人也能一枪打上?
刘大松说,我这把枪不错,只要能瞄上,就能打上。
老聂说,这样吧,你们先抓紧休息,可能半夜就要出发。我家地窖里还有点吃的,明天一起扛上山,可以多顶两天。我去找个人,半夜前能回来。小赵,有几句话跟你说一下。
领着大家把地窖里的食物取出之后,老聂就匆匆走了。大家在屋里休息,刘大松和赵腊梅两人来到小棚子,扒拉些草秸作铺垫,并肩坐下。
刘大松问,老聂说了什么。
赵腊梅说,问你的事吧。老聂说,要赶快把你送走产。我说,怎么走呀?前山出不云。就是出去了,都是鬼子二铬子。从后山爬悬崖,多危险呀。留下也不错吗,能给我们撑个腰。老聂批评我了,说我有本位主义。
刘大松没听说过这个词,不明白是什么意思。
赵腊梅解释说,就是光考虑自己这方面。
刘大松觉得好玩,地方上的东西真是跟队伍上的有许多不同,我们叫个人主义。
赵腊梅一边比划,一边解释,个人主义小,本位主义大。比方说,你是部队上的,我是地方上的,咱们的工作都是蒸干粮,我这忙不过来,就把你抓来帮忙,结果我的干粮蒸好了,你那灶还没生火呢。
刘大松明白了这帽子是什么色,但没有明白为什么要戴这帽子,老聂批评你这干吗?
赵腊梅说,老聂觉得你是个人才,是我拖累了你。明天要是光藏不打呢,你白跟我们受窝囊气,吃苦受累的不说,还要耽误回部队的时间。要是真刀真枪的干呢,我们只能跑龙套,敲边鼓,这二三十个鬼子二狗子要全靠你一个人顶着。老聂的意思是让我劝你走,回队伍上去。
刘大松说,有一个事情一直不明白,又不好问老聂,咱们为什么不一块走呀?非在这沟里等着人家来呀。赵腊梅说,好走不就早走了吗?东边人家堵着呢。往南往北,要翻山不说,翻来翻去,还是在人家的地盘里。往西呀,那是悬崖,下去了就再也上不来了。山那边是静宁的地盘,不是西忻的。不到万不得已,不能走这一步。
刘大松说,既然这样,我现在就死心塌地跟着你赵干事啦,先打了明天这仗再说。要是能活下来,我再回队伍去。
赵腊梅笑了,这么坚决。
刘大松说,那可不。头一个,我不应该跑,这饼子那来的,老乡从自己嘴里抠出来的,我吃完了,一抹嘴就走,太不地道了。二来呢,这跑了其实也不合算。要是跑的话,我现在就得还山门村走,我到了呢,大概人家也到了,我还得找个地方趴着,让人家先进来。这一折腾,天亮前到咱们自己地盘根本就没门。从芦芽山出来两天多,就在路东的山上眯了那么一下,今天再赶一晚夜路,明天恐怕就算是腿听话,脑袋也不听话啦。要是在哪个草堆睡觉时,叫人家小绳一捆抓了去,那死得多窝囊呀。
刘大松一席话,说得赵腊梅乐哈哈,你呀,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的。就是我笨,不会打枪,要是能跟李林一样就好了。李林是谁你知道吧?
刘大松说,知道,雁北那边的,骑兵营教导员。他们过路南的时候,我接过一次,没看清本人。
赵腊梅叹息道,能文能武的,真可惜的,死的时候还有三个月的身孕呢。你是怎么学会打枪的?我是说,你是怎么能打得这么准?我是不是也能学会?
刘大松说,在段和尚的队伍上没什么象样的训练,我说过吧,我开始不是入的咱们八路军。后来进了三支队,训练的时候,老兵就说我是打枪的料。他们说打枪与赶车有许多相同,主要是眼到手到。再就一眼就能看出有多远,调准标尺。还有眼睛能盯住东西,还有要算风有多大。
赵腊梅听着有趣,你以前是赶大车的?
刘大松说,是啊。这打枪吧,大劲小劲都要有。有人是大劲不够,枪举不稳。有人是小劲不行,搂扳机是两道火,有的人死活搂不出来,扣板机太猛了,枪口就会动。眼睛能盯住东西也是一样,有的人看东西不能看久了,稍微一久就花掉了。
赵腊梅说,我练过画画,能盯住东西,细巧劲我也有,别说两道火,就是八道火我也能搂出来。嗨,我就是没劲,揣不稳枪。要是把枪架好了,我一定能打得准准的。
刘大松说,你可以打重机枪呀。领导说,抢占阵地。大家上去把枪一架,子弹一挂。领导问,怎么不开火呀?这边说啦,报告领导,射手还没有上来呢。领导问,射手干什么去啦?这边说,射手摔了个跟头,把鞋子摔掉了,正满地找哪。
赵腊梅从地上弹了起来,你个死大刘,拿我来开心。说着就朝着刘大松的肩膀上捶了一家伙。
赵腊梅打的并不重,可刘大松却感到全身一颤,一股麻苏苏的劲从上一下子从头顶贯穿到脚底。
再看赵腊梅,她木头一般地呆在那。片刻,她又坐了回去,把头埋在膝盖里,双手紧紧抱着腿,肩膀一抖一颤的。过了半晌,肩膀不颤了,她抬起头,两眼直视前方,平淡的说,你赶快睡吧,一会儿还要站岗呢。
 收藏
收藏  打赏
打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