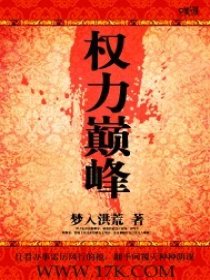正文:引子
引子
我在电脑前开始打这些文字的四五年前,中学同学聚会,他们问到了我的电话,打电话过来要我去参加。但我怎么会去参加呢?
他们一个个不是大款就起码也是县镇级的官员,还有局长级的,也还有贵为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的。而我,这时候还只是一个在乡下教书的民办教师,那是实实在在的贫民和穷人,社会弱势群体,社会最底层。而他们呢,都是成功人士,精英阶层,中上流社会。
同学聚会,虽然学生时代彼此之间也许会有点纯真的东西,但大家都出生社会这么多年了,这么多年没有联络和交往,现如今突然在一起,在一起会干什么呢?能干什么呢?难道主要的不会是比较谁活得成功,谁混得有名堂,而当今时代,所谓成功、有名堂那不就看你是不是大款,是不是当官的,是不是有身份有地位的吗?而我有这些东西吗?
如果你一身沧桑蹇困地站在他们面前,心不在焉,因为你还在为上普通中学的孩子的学费从哪里来、母亲住院向别人借的钱怎么还上发愁,不知道他们要你也品尝品尝的高级红酒怎么喝,不敢不听你本来可以混得比谁都成功、当年看哪个也不会有你前途远大、而今你怎么就混成这样子关切喟叹的议论,即使你被允许为自己辩护,但你的一切辩护对于他们都注定是苍白的,让他们更加可怜地看你,还要给你讲一些在当今时代和当今中国做人做事的大道理,不允许你不点头称是,你还会没事找事去参加他们的聚会吗?
物以类聚,人也群分。人这种动物,其实首先和主要地就是以其身价、地位来“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的,不然,只会让你尴尬别人也尴尬。
所以,我委婉地拒绝了他们的邀请。这实在是人之常情,也是为人之常道,换了任何人在我这种情况下都会这么做,除非他另有目的,或的确是太过另类。
不过,我虽没有去,到场的同学中却有一直和我走得比较近的,从离开学校后就从未断过联系。我就叫他程吧。程敢去参加这个同学聚会,还那样积极,不用说和他如今也赚到大钱了,算得上大款和成功人士了,和这些同学们大多有一比是直接相关的,也可以说他还就是为了去向昔日的同窗们展示展示“我如今也混出了名堂!”——大家都是饱经风霜的生活中人,用得着不承认事情就是这样的吗?
我的电话就是程提供给他们的。据程事后对我的描述,说同学们都很关心我如今在干什么,提到我的过去他们都很激动,说我当年如何如何突出优秀,所有老师和同学都认为我是“神童”,前途无量,但我不好好珍惜,以致落到今天这个下场。他们还真用的是“下场”这个词。
他们还都说当年他们就不认为我的一些做法和想法是对的,现在他们更认为我的那些做法和想法是错的。他们都为我感到惋惜。
我当年的什么做法和想法呢?
当年我就因为这些做法和想法而在地方上非常有名。当年我因两件事出了名,一件事就是我在学习上表现出了他们所说的“极高的智商”,我简直算得上“神童”,所有人都断言我是清华北大的苗子,还可能是未来的大科学家,前途无量云云;第二件事就是我因为同学们所说那些做法和想法而毁掉了自己的前程,灰溜溜地回家当了个农民。
我灰溜溜地离开学校回家当了农民后,听说我的母校,还专门召开学生大会,在会上把我树为反面典型。
说是校长亲自在会上讲,我不过是一个穷农民的儿子,我来到学校应该做的事情只有一件,那就是好好学习考上大学,改变自己的命运,也改变我的家庭状况,但是,我虽然是被老师们公认的读书学习方面的“神童”,清华北大的苗子,我却没有把心思用在学习上,不懂中国国情,无视物质决定精神、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现实规律,不知道我们先要解决物质贫乏的问题、解决肚子的问题才能谈理想、谈崇高的东西,进校没多久就高举自由和正义的大旗,高举维护做人的尊严和权利的大旗,做出了我们其他哪一个学生也不会做出的极端出格的事情,学校和老师们都关心我看重我,没有就这些事情处分我,只是从思想上帮助我和教育我,但是,我不仅没有接受这些帮助和教育,还变本加厉,越走越远,到最后,我不仅没有回头,还干脆放弃了学习,成了一混日子的学生,以示和学校对抗,学校因为还不愿意完全放弃对我的期望,再加上他们同情我的家庭和大多数来我们学校学习的农民孩子的家庭一样,是贫穷的农民家庭,才没有将我开除,但我却始终没有改变或改造自己的迹象,终于在高考中名落孙山,卷起铺盖回家了,云云。
“高举起自由和正义的大旗,高举维护做人的尊严和权利的大旗”,虽然我并没有亲耳听到我母校的校长这样说,它只是在我母校读书的同乡回来这么向村人们转述的,但是,我知道我母校的校长一定就是这样说的,也能够想象得到他这话一出口,全场的学生一定都笑了,那笑声就像一片云彩一样飘浮在会场上空久久不肯散去。当初,学校和老师们对我干的那么点事情本来也就是这么定性的。
三十年后同学们聚会,说我当年的做法和想法,想法也就是指我做那么些事情时,打着什么什么旗帜。校长说我进校没多久就怎么怎么的,实际却是我在做这些什么什么事时,既没有发表什么宣言,脑子里也没有什么“自由和正义”的想法,对于我,我只是被迫那样做而已,别无选择而已。是老师们说我打着这样的大旗。后来,那都是五年中学生活快结束了,我感觉到得为自己辩护了,才将就他们的话说,为“尊严和权利”做什么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和权利之类的话,但这更让他们抓住了把柄,我人都走了,回老家当农民了,都还要拿到全校的师生大会上让一校学生把我笑一通。
校长在大会的这套说法,其实一直就是所有的老师们和同学们,还有我家乡所有的村人们,还包括我家人、亲戚、朋友对我的说法,这套说法的中心思想、核心思想一直没有变,只是其内容在不断地丰富,到我高考名落孙山灰溜溜回家当了农民后时达到了顶点,不要说我母校以我为反面典型教育学生,我家乡的人们也都以我为反面典型教育他们的孩子。这个事情在我的家乡持续好多年,在好多年里我一出门碰到任何一个认识我的人,他们都会如同我脸上真刻着那么一行不光彩的字地看我,或议论我、开导我、教导我,就是如今我已是奔五十岁的人了,都还有可能听到有人提起我当年的那些做法和想法的确是错了。
为了生存,我回家务农后干起了在村上当民办代课老师的职业,家长们把孩子送到我班上来读书,很多家长都要我保证不要把我的思想传染给他们的孩子们,只是把我的知识传给他们的孩子们,他们的孩子到学校来只是为了将来有文化能在社会上比他们混得更好、更有出息,最好是能够考上大学离开农村改变他们和他们的家庭的命运,不是来为了我所说的那些真理、正义、自由、尊严、权利的东西,他们把孩子送到我班上来只是因为看重了我还是个有知识的人,我们村里确实找不到第二个比我有知识的人来教他们的孩子,云云。我为了生存和尊重他们,不得不做出庄重的承诺。
我得承认,我这一生都或多或少地生活在人们对我的这个说法和看法的阴影之中,就是一个三十年后的同学聚会,他们本是想不起那些如今混得落魄的同学的,却想起了我,想起了我还要把我当年提一提,提一提我当年“那些做法和想法的确是错了”。
然而,我却不得不说,这些说法在当年是那么多人那么热衷的话题,事过三十年了都还有人这么说,当年在学校的时候,可以说也就因为老师们总是这样批评和教育我,也许我在“变本加厉”,但老师们这方面对我的批评和教育也在“变本加厉”,到了我经常是一整星期一整星期地给他们写检讨书或一整天一整天地在他们办公室耳提面命听他们谆谆教导而不是在教室里听课做作业的地步,我才沦落为“放弃学习,成了一个混日子的学生”,但是,认真想一想,却不得不看到,当年可以归结为他们所说的“错误做法和想法”的事情是那样少,那样微不足道,校长在学生会上所说的我进校没多久就高举什么大旗做的那件事,的确可能是我那些“错误的做法”中最突出、最有代表性的一件事了,但是,就是它也是那样微不足道。
真的,它们的确是太微小、太一般、太平常了,微小、一般和平常得到了我不得不震惊的地步。总之,它们实在不配他们给它们戴这么高的帽子,事过三十年还要提及。
我在电脑前开始打这些文字的四五年前,中学同学聚会,他们问到了我的电话,打电话过来要我去参加。但我怎么会去参加呢?
他们一个个不是大款就起码也是县镇级的官员,还有局长级的,也还有贵为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的。而我,这时候还只是一个在乡下教书的民办教师,那是实实在在的贫民和穷人,社会弱势群体,社会最底层。而他们呢,都是成功人士,精英阶层,中上流社会。
同学聚会,虽然学生时代彼此之间也许会有点纯真的东西,但大家都出生社会这么多年了,这么多年没有联络和交往,现如今突然在一起,在一起会干什么呢?能干什么呢?难道主要的不会是比较谁活得成功,谁混得有名堂,而当今时代,所谓成功、有名堂那不就看你是不是大款,是不是当官的,是不是有身份有地位的吗?而我有这些东西吗?
如果你一身沧桑蹇困地站在他们面前,心不在焉,因为你还在为上普通中学的孩子的学费从哪里来、母亲住院向别人借的钱怎么还上发愁,不知道他们要你也品尝品尝的高级红酒怎么喝,不敢不听你本来可以混得比谁都成功、当年看哪个也不会有你前途远大、而今你怎么就混成这样子关切喟叹的议论,即使你被允许为自己辩护,但你的一切辩护对于他们都注定是苍白的,让他们更加可怜地看你,还要给你讲一些在当今时代和当今中国做人做事的大道理,不允许你不点头称是,你还会没事找事去参加他们的聚会吗?
物以类聚,人也群分。人这种动物,其实首先和主要地就是以其身价、地位来“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的,不然,只会让你尴尬别人也尴尬。
所以,我委婉地拒绝了他们的邀请。这实在是人之常情,也是为人之常道,换了任何人在我这种情况下都会这么做,除非他另有目的,或的确是太过另类。
不过,我虽没有去,到场的同学中却有一直和我走得比较近的,从离开学校后就从未断过联系。我就叫他程吧。程敢去参加这个同学聚会,还那样积极,不用说和他如今也赚到大钱了,算得上大款和成功人士了,和这些同学们大多有一比是直接相关的,也可以说他还就是为了去向昔日的同窗们展示展示“我如今也混出了名堂!”——大家都是饱经风霜的生活中人,用得着不承认事情就是这样的吗?
我的电话就是程提供给他们的。据程事后对我的描述,说同学们都很关心我如今在干什么,提到我的过去他们都很激动,说我当年如何如何突出优秀,所有老师和同学都认为我是“神童”,前途无量,但我不好好珍惜,以致落到今天这个下场。他们还真用的是“下场”这个词。
他们还都说当年他们就不认为我的一些做法和想法是对的,现在他们更认为我的那些做法和想法是错的。他们都为我感到惋惜。
我当年的什么做法和想法呢?
当年我就因为这些做法和想法而在地方上非常有名。当年我因两件事出了名,一件事就是我在学习上表现出了他们所说的“极高的智商”,我简直算得上“神童”,所有人都断言我是清华北大的苗子,还可能是未来的大科学家,前途无量云云;第二件事就是我因为同学们所说那些做法和想法而毁掉了自己的前程,灰溜溜地回家当了个农民。
我灰溜溜地离开学校回家当了农民后,听说我的母校,还专门召开学生大会,在会上把我树为反面典型。
说是校长亲自在会上讲,我不过是一个穷农民的儿子,我来到学校应该做的事情只有一件,那就是好好学习考上大学,改变自己的命运,也改变我的家庭状况,但是,我虽然是被老师们公认的读书学习方面的“神童”,清华北大的苗子,我却没有把心思用在学习上,不懂中国国情,无视物质决定精神、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现实规律,不知道我们先要解决物质贫乏的问题、解决肚子的问题才能谈理想、谈崇高的东西,进校没多久就高举自由和正义的大旗,高举维护做人的尊严和权利的大旗,做出了我们其他哪一个学生也不会做出的极端出格的事情,学校和老师们都关心我看重我,没有就这些事情处分我,只是从思想上帮助我和教育我,但是,我不仅没有接受这些帮助和教育,还变本加厉,越走越远,到最后,我不仅没有回头,还干脆放弃了学习,成了一混日子的学生,以示和学校对抗,学校因为还不愿意完全放弃对我的期望,再加上他们同情我的家庭和大多数来我们学校学习的农民孩子的家庭一样,是贫穷的农民家庭,才没有将我开除,但我却始终没有改变或改造自己的迹象,终于在高考中名落孙山,卷起铺盖回家了,云云。
“高举起自由和正义的大旗,高举维护做人的尊严和权利的大旗”,虽然我并没有亲耳听到我母校的校长这样说,它只是在我母校读书的同乡回来这么向村人们转述的,但是,我知道我母校的校长一定就是这样说的,也能够想象得到他这话一出口,全场的学生一定都笑了,那笑声就像一片云彩一样飘浮在会场上空久久不肯散去。当初,学校和老师们对我干的那么点事情本来也就是这么定性的。
三十年后同学们聚会,说我当年的做法和想法,想法也就是指我做那么些事情时,打着什么什么旗帜。校长说我进校没多久就怎么怎么的,实际却是我在做这些什么什么事时,既没有发表什么宣言,脑子里也没有什么“自由和正义”的想法,对于我,我只是被迫那样做而已,别无选择而已。是老师们说我打着这样的大旗。后来,那都是五年中学生活快结束了,我感觉到得为自己辩护了,才将就他们的话说,为“尊严和权利”做什么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和权利之类的话,但这更让他们抓住了把柄,我人都走了,回老家当农民了,都还要拿到全校的师生大会上让一校学生把我笑一通。
校长在大会的这套说法,其实一直就是所有的老师们和同学们,还有我家乡所有的村人们,还包括我家人、亲戚、朋友对我的说法,这套说法的中心思想、核心思想一直没有变,只是其内容在不断地丰富,到我高考名落孙山灰溜溜回家当了农民后时达到了顶点,不要说我母校以我为反面典型教育学生,我家乡的人们也都以我为反面典型教育他们的孩子。这个事情在我的家乡持续好多年,在好多年里我一出门碰到任何一个认识我的人,他们都会如同我脸上真刻着那么一行不光彩的字地看我,或议论我、开导我、教导我,就是如今我已是奔五十岁的人了,都还有可能听到有人提起我当年的那些做法和想法的确是错了。
为了生存,我回家务农后干起了在村上当民办代课老师的职业,家长们把孩子送到我班上来读书,很多家长都要我保证不要把我的思想传染给他们的孩子们,只是把我的知识传给他们的孩子们,他们的孩子到学校来只是为了将来有文化能在社会上比他们混得更好、更有出息,最好是能够考上大学离开农村改变他们和他们的家庭的命运,不是来为了我所说的那些真理、正义、自由、尊严、权利的东西,他们把孩子送到我班上来只是因为看重了我还是个有知识的人,我们村里确实找不到第二个比我有知识的人来教他们的孩子,云云。我为了生存和尊重他们,不得不做出庄重的承诺。
我得承认,我这一生都或多或少地生活在人们对我的这个说法和看法的阴影之中,就是一个三十年后的同学聚会,他们本是想不起那些如今混得落魄的同学的,却想起了我,想起了我还要把我当年提一提,提一提我当年“那些做法和想法的确是错了”。
然而,我却不得不说,这些说法在当年是那么多人那么热衷的话题,事过三十年了都还有人这么说,当年在学校的时候,可以说也就因为老师们总是这样批评和教育我,也许我在“变本加厉”,但老师们这方面对我的批评和教育也在“变本加厉”,到了我经常是一整星期一整星期地给他们写检讨书或一整天一整天地在他们办公室耳提面命听他们谆谆教导而不是在教室里听课做作业的地步,我才沦落为“放弃学习,成了一个混日子的学生”,但是,认真想一想,却不得不看到,当年可以归结为他们所说的“错误做法和想法”的事情是那样少,那样微不足道,校长在学生会上所说的我进校没多久就高举什么大旗做的那件事,的确可能是我那些“错误的做法”中最突出、最有代表性的一件事了,但是,就是它也是那样微不足道。
真的,它们的确是太微小、太一般、太平常了,微小、一般和平常得到了我不得不震惊的地步。总之,它们实在不配他们给它们戴这么高的帽子,事过三十年还要提及。
 收藏
收藏  打赏
打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