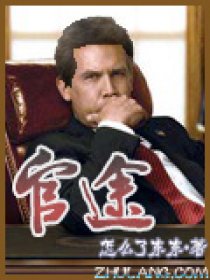朋友
在我的心里,始终装着一位朋友。尽管分手二十三年了,但心中仍有淡淡的牵挂、淡淡的思念;尽管中国不是很大,相隔路途也许不是很远,可一直没能相见,也没再有她的消息;尽管生活忙忙碌碌,日子匆匆而过,可对朋友的思念从没有间断过。
她是我们学校新来的老师,叫杨凡。高高的个儿,发卡将齐肩的卷发拢在耳后,显得近视镜上方的额头更饱满了,平静的脸上常带着笑意,说话很谦和。她教生物,但不教我,好象是因为我俩都喜欢学英语,不知不觉就好到一起了。
有时周末,她带我去她家里玩。她家除了她们三个孩子和她母亲,几乎是一贫如洗,仅有的贵重家具就是一个粟色的通长的连体的四个木箱子,屋子倒是干净得一尘不染,家里静静的。她又领我去了她妈妈单位,她妈妈是照相馆的会计,她父亲在她弟弟才三岁的时候就过世了,她妈妈一直领着她们姐弟仨过,当时她妹妹上大三,弟弟刚读大一,用她的话说,家里特拮据。可尽管在这样的单亲家庭,她虽朴素些,看上去还是很乐观,虽然很平和,但看上去还是很浪漫。
我俩除了聊学英语,也在一起散步,路上见了,彼此都特开心,尽管常在学校见面。她酷爱学习,常常看她手里拿着卷着的资料走着。一见到她,我就象见了迎面而来的春风,特别的惬意。有空闲的时候,她常约我聊天,聊她妈妈有多辛苦,聊对她爸没多深记忆,聊她们姐弟是多么努力学习,聊她还没有男朋友,聊她还是爱学习。
和她在一起的日子,我很开心,很踏实,觉着她象姐姐一样亲切,尽管我没有姐姐,不知姐姐是什么感觉。临毕业了,她约我去照相馆照了一张合影,我俩拉着手,亲密地拥站在一起,都带着眼镜,她穿一身休闲服,我穿了一条牛仔裤和一件胸前带着小红花的白色上衣,我俩目视前方,都微笑着。
在这么多年里,一听到有叫杨凡的,不管是男的还是女的,都觉得特亲切。记得我毕业时,她送我一个日记本,扉页上写到“人在一生里的时间是有限的,我们要把有限的时间用在做世上最有意义的事情上。——斯宾塞”,至今记忆犹新,一直用这句话警示自己。朋友,在心里淡淡的,淡淡的,象水一样,思念,牵挂,不知什么时候能再相遇?
她是我们学校新来的老师,叫杨凡。高高的个儿,发卡将齐肩的卷发拢在耳后,显得近视镜上方的额头更饱满了,平静的脸上常带着笑意,说话很谦和。她教生物,但不教我,好象是因为我俩都喜欢学英语,不知不觉就好到一起了。
有时周末,她带我去她家里玩。她家除了她们三个孩子和她母亲,几乎是一贫如洗,仅有的贵重家具就是一个粟色的通长的连体的四个木箱子,屋子倒是干净得一尘不染,家里静静的。她又领我去了她妈妈单位,她妈妈是照相馆的会计,她父亲在她弟弟才三岁的时候就过世了,她妈妈一直领着她们姐弟仨过,当时她妹妹上大三,弟弟刚读大一,用她的话说,家里特拮据。可尽管在这样的单亲家庭,她虽朴素些,看上去还是很乐观,虽然很平和,但看上去还是很浪漫。
我俩除了聊学英语,也在一起散步,路上见了,彼此都特开心,尽管常在学校见面。她酷爱学习,常常看她手里拿着卷着的资料走着。一见到她,我就象见了迎面而来的春风,特别的惬意。有空闲的时候,她常约我聊天,聊她妈妈有多辛苦,聊对她爸没多深记忆,聊她们姐弟是多么努力学习,聊她还没有男朋友,聊她还是爱学习。
和她在一起的日子,我很开心,很踏实,觉着她象姐姐一样亲切,尽管我没有姐姐,不知姐姐是什么感觉。临毕业了,她约我去照相馆照了一张合影,我俩拉着手,亲密地拥站在一起,都带着眼镜,她穿一身休闲服,我穿了一条牛仔裤和一件胸前带着小红花的白色上衣,我俩目视前方,都微笑着。
在这么多年里,一听到有叫杨凡的,不管是男的还是女的,都觉得特亲切。记得我毕业时,她送我一个日记本,扉页上写到“人在一生里的时间是有限的,我们要把有限的时间用在做世上最有意义的事情上。——斯宾塞”,至今记忆犹新,一直用这句话警示自己。朋友,在心里淡淡的,淡淡的,象水一样,思念,牵挂,不知什么时候能再相遇?
 收藏
收藏  打赏
打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