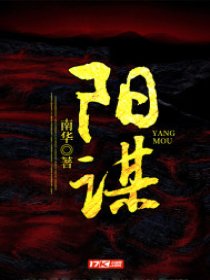正文:17、谁都在犯平庸之罪
郑航理解了方娟痛苦不堪的原因,心中不免对这个倔强的女孩产生敬意。
在物欲横流的社会,只有爱和责任最为宝贵。
“去年他就在考验我了。”她猛地抬起身,随后就颓然倒在沙发上。“我自以为聪明,可没想到败得很惨,甚至没有入门。”
郑航掏出一支烟,想了想,又摁在烟灰缸里。“方主任,我很理解你此刻的心情。别说是你,就是多年在恶性案件中打滚的老刑警,如果有个这样的对手,一样会感到震惊。但震惊归震惊……”
方娟白了一他一眼,爆出一句粗口:“啰嗦有个屁用。”
郑航尽力压住火气。“我很理解你的心情……”
“我不需要你的理解,我只是在想他为什么要杀那么多的人!如果是针对我,针对社区自愿戒毒管理中心,那直接来啊,为什么要白白搭上那么多人的性命?”
“不要去想那些已经死去的人了,死了就是死了,他们谁也不会因为你的内疚而起死回生。这就是他们的命运。既然你知道了这么多内情,那么,在他杀死更多的人之前阻止他,抓住他,这才是对死者最好的安慰。”
“对。”方娟凝视了郑航几秒钟,一把抓住他的手,这个举动让他俩都吃了一惊。
“刘志文死了,黄绸手绢出现,可以肯定是连环杀手干的。时间迫在眉睫,公道自在人心。接下来,我有事情请你帮忙。”
10
不知什么时候,窗外下起了暴雨,天空变得沉重而阴森。
郑航和方娟一直坐在咖啡馆里,等待刑侦的勘验结论。虽然方娟指认了死者的身份,但要获得法定认可,还要结合DNA和指纹的比对鉴定。
有那么一段时间,他们什么话儿都没有说。方娟看着窗外的狂风夹杂着暴雨打着旋儿肆虐;郑航的思绪随着风雨,到了一个极其悲伤的地方。
不知沉思了多长时间。方娟说:“我知道了你的身世。”
这话一下子控制住他的整个身心,好像身体里的另一个郑航在不经意间悄悄冒了出来。他的全部思维都随着这个郑航的出现而被调动起来。他想到了母亲。母亲的忧郁不是一天形成的,父亲的死只是一颗种子,时间才是化雨春风,慢慢地发芽,抽枝长叶,最终茁壮成参天大树,把母亲带了去。
这感觉让他惶恐。
“你觉得每天接触凶杀案会改变你吗?”郑航捏了捏眉心,答非所问地说。“我是说,一边你是个女孩,以后会结婚,会生儿女,一边你得出去逮捕杀人犯,包括涉及妇女儿童的杀人犯,或者是处理绑架妇女儿童的案子,连环性侵案件,纵火案,或者别的有关妇女儿童的案件,你感觉会怎么样?”
方娟小声地说:“你怎么突然这样想?”
“我觉得你是个感情丰富的女孩。你在外面办了那些案子,然后回到家带儿女,给丈夫做饭,你觉得能洗掉那些案子带给你手上的气味吗?更不用说抹去脑海里的印象。”
“我想,我能。”
“女人真能这样完成角色转换吗?”
“家庭会给我带来无穷的乐趣,儿女更能让我忘掉其他的事情。”
郑航皱眉看着方娟,显然不想接着讨论下去,接着看暴风雨。过了一会儿,方娟凑过来,拿起郑航的手摇晃。“你在想什么呢?这个案子吗?”
“是的。”郑航缩回手,“我觉得你既做得对,又不对。刑侦部门是关键。你以前听说过平庸之恶吗,方娟?”
“平庸之恶?”
“也有人称之为平庸之罪。”
“你说的是那个德国纳粹分子阿道夫?艾希曼。”
“是啊。犹太裔著名政治思想家汉娜·阿伦特在《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关于艾希曼审判的报告》里描述审判席上的纳粹党徒艾希曼,‘不阴险,也不凶横’,完全不像一个恶贯满盈的刽子手,‘他的一生都是依据康德的道德律令而活,他所有行动都来自康德对于责任的界定。’‘他所做的都是当时国家法律所允许的;作为一名军人,他只是在服从和执行上级的命令。’阿伦特据此提出了著名的‘平庸之恶’概念,认为这种恶是不思考人,不思考社会。恶是平庸的,因为你我常人,都可能堕入其中。”
方娟嘟囔了一句:“它是相对于‘极端之恶’说的。”
“它其实揭示了人类的本性。这样的恶是不曾思考过的东西,就像覆盖在毒菇表面的霉菌那样繁衍,可以发生在每一个人身上。比如在这系列案件中,刑警可能就在确凿的证据面前失去了自己的判断能力。”
“你这是转着弯儿表扬我呢。”
郑航耸耸肩。“谁说我在表扬你了?这是生活的真相。你我都生活在体制中,每个人都在附和它,仅仅是因为不想与他人不同,只想做个顺应他人的‘好人’,所以每个人都可能犯‘平庸之恶’。恶是不用思考的,只有善才有深度,才是本质。”
“我即不希望犯平庸之恶,也不想有平庸的英雄主义。”
郑航嘲谑地说:“拜托,别说你想当超人。”
“实际上,我只想当一个理想的警察。我会在地铁站台上扶起摔倒的乘客,也会在街头救助不幸走失的小孩……我想,用勇敢的举动,应对人生中随时可能发生的残酷事件,这也是人类的本性。”
郑航看着窗外渐渐小起来的风雨,说:“你让我看到了阳光。”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郑航。”不知不觉中,他们彼此直呼其名了。
郑航脸红了。他有点不知所措,方娟的话是针对他的身世说的,他觉得方娟小看了他,说他不够坚强。他应该说些什么,挽回自己在方娟心里的形象。
但是他没有说,看着方娟富有女性特征的脸。她的手指在大腿上不停地摆弄。
郑航猛地意识到,也是第一次意识到——平庸之恶,不就是说的现在坐在这里的自己吗?不加思考地跟着别人的想法走,不加思索地赢得同情,如果时机合适,不论那些想法正确与否,都会随大流地去做。因为在很久以前发生的家庭灾难,受到的伤害,或者是心底的愤怒,自己无能为力,只能舔舐自己的伤口,所以内心充满深深的、无止境的、希望得到别人认同,或者同情的渴望。
郑航吓了一跳。他感到害怕了。他想起一本外国著作里的话:大部分人根本用不着陌生人做出残酷的事来打乱他们的生活,他们自己就有毁灭自己生活的能力。
方娟转过身,盯着郑航,乌黑晶亮的眼睛让人读不懂。郑航能感觉到她的真诚、紧张,还有一往无前的执着。
雨还没有彻底停,太阳就出来了,照得窗台亮晃晃的,停车场外可以看到彩虹的脚印。这时,方娟的手机响了。齐胜来的电话,告诉他已经确认了刘志文的身份。
“调查民警准备去走访他家,你有没有时间?”
“我正等着呢,还有辖区派出所的郑航副所长。”
刘志文的家离咖啡馆不远,在临津门二号巷。说是家,其实只是两间煤房,正式的住宅早在八年前就卖掉了,那时他正吸毒。
方娟没有取她的摩托车,而是与郑航步行过去,这样更节省时间。打老远,她就望见那幢房子。停住脚步,后面响起停车声,是两名调查刑警。
这里是辰河市印刷厂家属院,大概修建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工厂早于八十年代末倒闭了,院里的住户也换了几代人。四层小楼,赭色的墙,黑色的瓦,很破落的样子。
楼前一排加修的煤房,有个火柴棍似的男人在房前烧火,大概是想把煤炉点燃。他吃惊地看着身材窈窕的方娟,慌慌地站起来,点头哈腰地招呼。
“方……方主任,您有事?”
方娟迟疑片刻,然后介绍了两位刑警,并直接了当地问:“您跟志佬住在一起?”
“志叔收容了我。”火柴棍说,“不仅我,还有计伢子、黄毛、爱军、莫爷,都住在这里。你不是教导我们要抱团取暖吗?这个冬天我们就是这样做的。”
他大约四十岁左右,瘦瘦的个子,脸上布满皱纹,两只灰灰的眼睛带着探询讨好的神情,望着方娟和两名刑警。
这时,从屋里走来一个柱拐杖的男孩,右脚重度残疾。
方娟思索着该说些什么。她走在路上时就在考虑,但还是不知道该怎么说才好。
“是不是找志叔有事?”那人问,又探询地望着方娟。
“除了你们,志佬还有没有其他亲人?”方娟问。
男孩走到火柴棍前面,抢着说:“权哥,这个我知道。我跟了志爸几年,从没看他去看望什么亲人,也没看到有什么人来看望过他。”
“这是计伢子,以前总在街头乞讨过活。志叔看到后,把他带回了家,照顾他。”
“志爸出什么事了吗?”计伢子问。
在物欲横流的社会,只有爱和责任最为宝贵。
“去年他就在考验我了。”她猛地抬起身,随后就颓然倒在沙发上。“我自以为聪明,可没想到败得很惨,甚至没有入门。”
郑航掏出一支烟,想了想,又摁在烟灰缸里。“方主任,我很理解你此刻的心情。别说是你,就是多年在恶性案件中打滚的老刑警,如果有个这样的对手,一样会感到震惊。但震惊归震惊……”
方娟白了一他一眼,爆出一句粗口:“啰嗦有个屁用。”
郑航尽力压住火气。“我很理解你的心情……”
“我不需要你的理解,我只是在想他为什么要杀那么多的人!如果是针对我,针对社区自愿戒毒管理中心,那直接来啊,为什么要白白搭上那么多人的性命?”
“不要去想那些已经死去的人了,死了就是死了,他们谁也不会因为你的内疚而起死回生。这就是他们的命运。既然你知道了这么多内情,那么,在他杀死更多的人之前阻止他,抓住他,这才是对死者最好的安慰。”
“对。”方娟凝视了郑航几秒钟,一把抓住他的手,这个举动让他俩都吃了一惊。
“刘志文死了,黄绸手绢出现,可以肯定是连环杀手干的。时间迫在眉睫,公道自在人心。接下来,我有事情请你帮忙。”
10
不知什么时候,窗外下起了暴雨,天空变得沉重而阴森。
郑航和方娟一直坐在咖啡馆里,等待刑侦的勘验结论。虽然方娟指认了死者的身份,但要获得法定认可,还要结合DNA和指纹的比对鉴定。
有那么一段时间,他们什么话儿都没有说。方娟看着窗外的狂风夹杂着暴雨打着旋儿肆虐;郑航的思绪随着风雨,到了一个极其悲伤的地方。
不知沉思了多长时间。方娟说:“我知道了你的身世。”
这话一下子控制住他的整个身心,好像身体里的另一个郑航在不经意间悄悄冒了出来。他的全部思维都随着这个郑航的出现而被调动起来。他想到了母亲。母亲的忧郁不是一天形成的,父亲的死只是一颗种子,时间才是化雨春风,慢慢地发芽,抽枝长叶,最终茁壮成参天大树,把母亲带了去。
这感觉让他惶恐。
“你觉得每天接触凶杀案会改变你吗?”郑航捏了捏眉心,答非所问地说。“我是说,一边你是个女孩,以后会结婚,会生儿女,一边你得出去逮捕杀人犯,包括涉及妇女儿童的杀人犯,或者是处理绑架妇女儿童的案子,连环性侵案件,纵火案,或者别的有关妇女儿童的案件,你感觉会怎么样?”
方娟小声地说:“你怎么突然这样想?”
“我觉得你是个感情丰富的女孩。你在外面办了那些案子,然后回到家带儿女,给丈夫做饭,你觉得能洗掉那些案子带给你手上的气味吗?更不用说抹去脑海里的印象。”
“我想,我能。”
“女人真能这样完成角色转换吗?”
“家庭会给我带来无穷的乐趣,儿女更能让我忘掉其他的事情。”
郑航皱眉看着方娟,显然不想接着讨论下去,接着看暴风雨。过了一会儿,方娟凑过来,拿起郑航的手摇晃。“你在想什么呢?这个案子吗?”
“是的。”郑航缩回手,“我觉得你既做得对,又不对。刑侦部门是关键。你以前听说过平庸之恶吗,方娟?”
“平庸之恶?”
“也有人称之为平庸之罪。”
“你说的是那个德国纳粹分子阿道夫?艾希曼。”
“是啊。犹太裔著名政治思想家汉娜·阿伦特在《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关于艾希曼审判的报告》里描述审判席上的纳粹党徒艾希曼,‘不阴险,也不凶横’,完全不像一个恶贯满盈的刽子手,‘他的一生都是依据康德的道德律令而活,他所有行动都来自康德对于责任的界定。’‘他所做的都是当时国家法律所允许的;作为一名军人,他只是在服从和执行上级的命令。’阿伦特据此提出了著名的‘平庸之恶’概念,认为这种恶是不思考人,不思考社会。恶是平庸的,因为你我常人,都可能堕入其中。”
方娟嘟囔了一句:“它是相对于‘极端之恶’说的。”
“它其实揭示了人类的本性。这样的恶是不曾思考过的东西,就像覆盖在毒菇表面的霉菌那样繁衍,可以发生在每一个人身上。比如在这系列案件中,刑警可能就在确凿的证据面前失去了自己的判断能力。”
“你这是转着弯儿表扬我呢。”
郑航耸耸肩。“谁说我在表扬你了?这是生活的真相。你我都生活在体制中,每个人都在附和它,仅仅是因为不想与他人不同,只想做个顺应他人的‘好人’,所以每个人都可能犯‘平庸之恶’。恶是不用思考的,只有善才有深度,才是本质。”
“我即不希望犯平庸之恶,也不想有平庸的英雄主义。”
郑航嘲谑地说:“拜托,别说你想当超人。”
“实际上,我只想当一个理想的警察。我会在地铁站台上扶起摔倒的乘客,也会在街头救助不幸走失的小孩……我想,用勇敢的举动,应对人生中随时可能发生的残酷事件,这也是人类的本性。”
郑航看着窗外渐渐小起来的风雨,说:“你让我看到了阳光。”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郑航。”不知不觉中,他们彼此直呼其名了。
郑航脸红了。他有点不知所措,方娟的话是针对他的身世说的,他觉得方娟小看了他,说他不够坚强。他应该说些什么,挽回自己在方娟心里的形象。
但是他没有说,看着方娟富有女性特征的脸。她的手指在大腿上不停地摆弄。
郑航猛地意识到,也是第一次意识到——平庸之恶,不就是说的现在坐在这里的自己吗?不加思考地跟着别人的想法走,不加思索地赢得同情,如果时机合适,不论那些想法正确与否,都会随大流地去做。因为在很久以前发生的家庭灾难,受到的伤害,或者是心底的愤怒,自己无能为力,只能舔舐自己的伤口,所以内心充满深深的、无止境的、希望得到别人认同,或者同情的渴望。
郑航吓了一跳。他感到害怕了。他想起一本外国著作里的话:大部分人根本用不着陌生人做出残酷的事来打乱他们的生活,他们自己就有毁灭自己生活的能力。
方娟转过身,盯着郑航,乌黑晶亮的眼睛让人读不懂。郑航能感觉到她的真诚、紧张,还有一往无前的执着。
雨还没有彻底停,太阳就出来了,照得窗台亮晃晃的,停车场外可以看到彩虹的脚印。这时,方娟的手机响了。齐胜来的电话,告诉他已经确认了刘志文的身份。
“调查民警准备去走访他家,你有没有时间?”
“我正等着呢,还有辖区派出所的郑航副所长。”
刘志文的家离咖啡馆不远,在临津门二号巷。说是家,其实只是两间煤房,正式的住宅早在八年前就卖掉了,那时他正吸毒。
方娟没有取她的摩托车,而是与郑航步行过去,这样更节省时间。打老远,她就望见那幢房子。停住脚步,后面响起停车声,是两名调查刑警。
这里是辰河市印刷厂家属院,大概修建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工厂早于八十年代末倒闭了,院里的住户也换了几代人。四层小楼,赭色的墙,黑色的瓦,很破落的样子。
楼前一排加修的煤房,有个火柴棍似的男人在房前烧火,大概是想把煤炉点燃。他吃惊地看着身材窈窕的方娟,慌慌地站起来,点头哈腰地招呼。
“方……方主任,您有事?”
方娟迟疑片刻,然后介绍了两位刑警,并直接了当地问:“您跟志佬住在一起?”
“志叔收容了我。”火柴棍说,“不仅我,还有计伢子、黄毛、爱军、莫爷,都住在这里。你不是教导我们要抱团取暖吗?这个冬天我们就是这样做的。”
他大约四十岁左右,瘦瘦的个子,脸上布满皱纹,两只灰灰的眼睛带着探询讨好的神情,望着方娟和两名刑警。
这时,从屋里走来一个柱拐杖的男孩,右脚重度残疾。
方娟思索着该说些什么。她走在路上时就在考虑,但还是不知道该怎么说才好。
“是不是找志叔有事?”那人问,又探询地望着方娟。
“除了你们,志佬还有没有其他亲人?”方娟问。
男孩走到火柴棍前面,抢着说:“权哥,这个我知道。我跟了志爸几年,从没看他去看望什么亲人,也没看到有什么人来看望过他。”
“这是计伢子,以前总在街头乞讨过活。志叔看到后,把他带回了家,照顾他。”
“志爸出什么事了吗?”计伢子问。
 收藏
收藏  打赏
打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