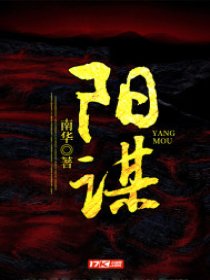披一身温暖的冬阳
“叮铃叮铃”闹钟的声音把我唤醒,我也不睁眼,就像梦游似的坐起,抓起枕边的毛衣,要往头上套。经常早起,改变的不只是我的生物钟,还使我养成了一种习惯,就像茅盾的《报施》中所写“半睡半醒,甚至嘴里还打着呼噜,他会穿衣服。”似的,完全不需要醒来,就可以干好多事,有的时候甚至牙都刷完了,还闭着眼睛。
可是,这次我的毛衣刚套了一半,却又突然睁眼看了一眼床头的台历,一看之下,刚刚套了一半的毛衣又一下子脱了下来,今天星期天——按照我的习惯,星期天是按照基督教中的习俗一样,是安息日。而我的安息,非常简单,就是睡觉。每次都要一直睡到上午十点才好,毕竟每天十一点钟睡觉,早上六点多起来,每天睡七个小时,对于我这种起床困难户来说,是非常痛苦的。然而,昨天也就是周六晚上我睡觉之前居然忘记了取消闹钟,于是今天早上我就悲剧的被闹钟唤醒了。
我不甘心,倒头又睡,可是我的睡眠还有一种相当特殊特点,每次早上不醒来便好,只要一醒来,那就很难再睡着了。于是,今天我的习惯又一次发作了,我翻来覆去的一直睡不着,就在床上烙饼。一直翻了半个小时,依然没有睡着,我一心急,索性决定不睡了。“扑棱”一下,坐起来,穿衣洗漱,一切事情都办妥之后,又觉得有点无聊了——我可以算是一个循规蹈矩的人,每件事都要严格的按照计划来进行,可是星期天的计划是按照十点半为开始制定的,现在才刚刚六点半,四个小时,我该怎么打发?
不管要干什么,先把窗帘拉开再说。窗帘一拉开,阳光随着窗帘的拉开“哗”的一下流进了房间里,洒在房间里,整个房间一下子装满了温暖的阳光。自从入冬以来,我的窗户一直被“八万天人”(我房间窗户上的冰花是一个一个的冰突起,就像攒动的人头,无法命名,冰突起数量又极多,索性就佛教典故取名为“八万天人”,估计佛祖要是听到非气活过来不可)牢牢地封锁着,把阳光牢牢地挡在外面。可是今天,或许是温度比较高的缘故,冰花居然化得一干二净,阳光就能够透进来了,从房间里,居然还能够看到屋外的蓝天。
帘子一拉开,阳光透进来,我蛰伏已久的一个爱好——散步,居然一下子从脑海中跳了出来。转念一想,正好时间没得打发,看这样子外面天气也并不很冷,就出去散散步吧,这几天在家里也憋闷坏了。
我向来不是一个磨蹭的人,决定了去散步,五分钟后我就已经出现在楼下了。外面并不很冷,虽然还是早晨,似乎比前几天的下午还要暖和一些——大概是前几日肆虐的“超级寒潮”已经过去的缘故吧。几天来一直没有下雪,所以地面还蛮干净,只有一些黑色的冰块,镶嵌在黑色的路上,就像古阿兹特克人用的剑——黑曜石的剑身上镶嵌着黑色的宝石。屋檐下,前几天好长的冰溜都已经融化了,然后又在地上冻成了一块钟乳石似的冰,这又像是远古的溶洞里才能见到的景象了——钟乳石上滴下石灰水,落到下面形成石笋。只不过,这里的冰并不像喀斯特地貌中的石灰水那样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所以,上面的“钟乳石”已经融化殆尽了,下面的石笋还只突起于地面一点点。当然,有些地方的冰还没有融化干净,显然是冻上的时候就很长了,此时檐上还留下一点点,正缓慢的往下滴着,滴在下面已经小有规模的“石笋”上了,发出“啪啪”的响声,然后那落下的一点水珠就一下子消失不见了,也不知是直接结冰,和下面的“石笋”融为一体了,亦或是顺着光滑的“石笋”表面流下去不知流到哪里去了。
冬天的早晨是很安静的,活了这么大,我还是头一次发现这一点。或许是因为以前冬天我都起得很晚,亦或者即使起早也没有出去的缘故吧——在家里只要外面的声音不超过五十分贝,在室内是绝对听不见的。本来冬天街上就没什么人,早上尤其如此,所以平时繁华喧闹的的声音自然是没有了,其他季节早晨的主要的声音来源是猫啊狗啊什么的,可是这些小动物一到了冬天就都躲进自己的巢穴里面去了,哪还会出来活动。于是,整个视野范围内,都是一片安宁祥和的寂静,在当今的城市里,这份寂静,自然是弥足珍贵的。说掉根针的声音都能听见那确实是有点夸张,但是,走在街上,我居然能清晰的听见自己的脚步声——我穿的不是皮鞋,是运动鞋。
不知不觉中居然走出了好远,等到我回过神来,一抬头间,发现自己居然已经来到了离家不远的小树林中了。此时的小树林,看上去是极为萧瑟的——叶子早就在深秋的风中陨灭了,近几天一直没有下一场雪,枝丫光秃秃的,树皮已经干得翘了起来。由于是早上,枝头别说是鸟,就是只苍蝇也没有——就算有我恐怕也未必看得见。太早了,打太极的老大爷还要过很久才能出来,于是,这片寂静的树林里就只剩下我一个人孤独的品味着嘴边白色的哈气。我似乎有点后悔,为什么非要这么早出来,躲在家里看会书不是很好吗,现在一个人在树林里受冻,连个说话的人也没有,就一个人在这里“吞云吐雾”。
这时候,我突然觉得背后暖洋洋的,很舒服,但又有些疑惑:这显然是与冬天这个名词相悖的。回头一看,顿时明白了。光秃秃的,不带一丝一毫叶子或是别的什么东西的枝桠把冬日的晨光切成一小块一小块的,就像一件格子披肩一样,披在我身上。这阳光,并不像平日里那样的清冷,而是带着些许的暖气,披上这一身阳光,总会使人产生一种错觉,好像春天就要来了似的。也难怪,这温暖而又和煦的阳光,哪里像是冬天,分明是初春嘛。而后突然间觉得很怪,平日里没少晒过太阳,可是那时候总觉得连阳光也被通天彻地的寒气冻住了似的,感觉不到什么温暖,按照常理,树林比街道应该只冷不热,刚一进来的时候感觉也确实如此,可是既然温度已经很低了,那么为什么阳光却是暖洋洋的呢?我不愿做过多的推测,我只相信眼前的这些老树的心和它们的枝条一样细,它们在把阳光漏成一件披肩的时候,还没忘了把朔风带来的寒气挡在树林外面。而它们做这些事情的目的,我想,或者我希望是想给像我一样的过路人一点温暖,一点春天的感觉。
一阵寒风吹过,我骤然惊醒,是啊,现在还是冬天,寒风刺骨的冬天。但是,这样一件阳光披肩带给我的,不仅是新奇,更多的是温暖,就像春天一样的温暖。这份温暖,大概不能缓解身体的寒冷——这毕竟还是冬天,但至少能够让我产生一种对春的向往,能让我想起英国诗人雪莱的那句“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
终于,我走出了小树林,因为我总不能一直占着那件披肩,总要让别人也享受一下这份温暖。刚从小道尽头转出来,迎面正撞见来打太极的老大爷,本想像往常一样低着头走过去,可是脑海中立刻又浮现出那件阳光做的披肩了。
“大爷,早啊。”我从大爷的眼睛里看到了我的笑容,很暖,就像那件披肩。
可是,这次我的毛衣刚套了一半,却又突然睁眼看了一眼床头的台历,一看之下,刚刚套了一半的毛衣又一下子脱了下来,今天星期天——按照我的习惯,星期天是按照基督教中的习俗一样,是安息日。而我的安息,非常简单,就是睡觉。每次都要一直睡到上午十点才好,毕竟每天十一点钟睡觉,早上六点多起来,每天睡七个小时,对于我这种起床困难户来说,是非常痛苦的。然而,昨天也就是周六晚上我睡觉之前居然忘记了取消闹钟,于是今天早上我就悲剧的被闹钟唤醒了。
我不甘心,倒头又睡,可是我的睡眠还有一种相当特殊特点,每次早上不醒来便好,只要一醒来,那就很难再睡着了。于是,今天我的习惯又一次发作了,我翻来覆去的一直睡不着,就在床上烙饼。一直翻了半个小时,依然没有睡着,我一心急,索性决定不睡了。“扑棱”一下,坐起来,穿衣洗漱,一切事情都办妥之后,又觉得有点无聊了——我可以算是一个循规蹈矩的人,每件事都要严格的按照计划来进行,可是星期天的计划是按照十点半为开始制定的,现在才刚刚六点半,四个小时,我该怎么打发?
不管要干什么,先把窗帘拉开再说。窗帘一拉开,阳光随着窗帘的拉开“哗”的一下流进了房间里,洒在房间里,整个房间一下子装满了温暖的阳光。自从入冬以来,我的窗户一直被“八万天人”(我房间窗户上的冰花是一个一个的冰突起,就像攒动的人头,无法命名,冰突起数量又极多,索性就佛教典故取名为“八万天人”,估计佛祖要是听到非气活过来不可)牢牢地封锁着,把阳光牢牢地挡在外面。可是今天,或许是温度比较高的缘故,冰花居然化得一干二净,阳光就能够透进来了,从房间里,居然还能够看到屋外的蓝天。
帘子一拉开,阳光透进来,我蛰伏已久的一个爱好——散步,居然一下子从脑海中跳了出来。转念一想,正好时间没得打发,看这样子外面天气也并不很冷,就出去散散步吧,这几天在家里也憋闷坏了。
我向来不是一个磨蹭的人,决定了去散步,五分钟后我就已经出现在楼下了。外面并不很冷,虽然还是早晨,似乎比前几天的下午还要暖和一些——大概是前几日肆虐的“超级寒潮”已经过去的缘故吧。几天来一直没有下雪,所以地面还蛮干净,只有一些黑色的冰块,镶嵌在黑色的路上,就像古阿兹特克人用的剑——黑曜石的剑身上镶嵌着黑色的宝石。屋檐下,前几天好长的冰溜都已经融化了,然后又在地上冻成了一块钟乳石似的冰,这又像是远古的溶洞里才能见到的景象了——钟乳石上滴下石灰水,落到下面形成石笋。只不过,这里的冰并不像喀斯特地貌中的石灰水那样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所以,上面的“钟乳石”已经融化殆尽了,下面的石笋还只突起于地面一点点。当然,有些地方的冰还没有融化干净,显然是冻上的时候就很长了,此时檐上还留下一点点,正缓慢的往下滴着,滴在下面已经小有规模的“石笋”上了,发出“啪啪”的响声,然后那落下的一点水珠就一下子消失不见了,也不知是直接结冰,和下面的“石笋”融为一体了,亦或是顺着光滑的“石笋”表面流下去不知流到哪里去了。
冬天的早晨是很安静的,活了这么大,我还是头一次发现这一点。或许是因为以前冬天我都起得很晚,亦或者即使起早也没有出去的缘故吧——在家里只要外面的声音不超过五十分贝,在室内是绝对听不见的。本来冬天街上就没什么人,早上尤其如此,所以平时繁华喧闹的的声音自然是没有了,其他季节早晨的主要的声音来源是猫啊狗啊什么的,可是这些小动物一到了冬天就都躲进自己的巢穴里面去了,哪还会出来活动。于是,整个视野范围内,都是一片安宁祥和的寂静,在当今的城市里,这份寂静,自然是弥足珍贵的。说掉根针的声音都能听见那确实是有点夸张,但是,走在街上,我居然能清晰的听见自己的脚步声——我穿的不是皮鞋,是运动鞋。
不知不觉中居然走出了好远,等到我回过神来,一抬头间,发现自己居然已经来到了离家不远的小树林中了。此时的小树林,看上去是极为萧瑟的——叶子早就在深秋的风中陨灭了,近几天一直没有下一场雪,枝丫光秃秃的,树皮已经干得翘了起来。由于是早上,枝头别说是鸟,就是只苍蝇也没有——就算有我恐怕也未必看得见。太早了,打太极的老大爷还要过很久才能出来,于是,这片寂静的树林里就只剩下我一个人孤独的品味着嘴边白色的哈气。我似乎有点后悔,为什么非要这么早出来,躲在家里看会书不是很好吗,现在一个人在树林里受冻,连个说话的人也没有,就一个人在这里“吞云吐雾”。
这时候,我突然觉得背后暖洋洋的,很舒服,但又有些疑惑:这显然是与冬天这个名词相悖的。回头一看,顿时明白了。光秃秃的,不带一丝一毫叶子或是别的什么东西的枝桠把冬日的晨光切成一小块一小块的,就像一件格子披肩一样,披在我身上。这阳光,并不像平日里那样的清冷,而是带着些许的暖气,披上这一身阳光,总会使人产生一种错觉,好像春天就要来了似的。也难怪,这温暖而又和煦的阳光,哪里像是冬天,分明是初春嘛。而后突然间觉得很怪,平日里没少晒过太阳,可是那时候总觉得连阳光也被通天彻地的寒气冻住了似的,感觉不到什么温暖,按照常理,树林比街道应该只冷不热,刚一进来的时候感觉也确实如此,可是既然温度已经很低了,那么为什么阳光却是暖洋洋的呢?我不愿做过多的推测,我只相信眼前的这些老树的心和它们的枝条一样细,它们在把阳光漏成一件披肩的时候,还没忘了把朔风带来的寒气挡在树林外面。而它们做这些事情的目的,我想,或者我希望是想给像我一样的过路人一点温暖,一点春天的感觉。
一阵寒风吹过,我骤然惊醒,是啊,现在还是冬天,寒风刺骨的冬天。但是,这样一件阳光披肩带给我的,不仅是新奇,更多的是温暖,就像春天一样的温暖。这份温暖,大概不能缓解身体的寒冷——这毕竟还是冬天,但至少能够让我产生一种对春的向往,能让我想起英国诗人雪莱的那句“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
终于,我走出了小树林,因为我总不能一直占着那件披肩,总要让别人也享受一下这份温暖。刚从小道尽头转出来,迎面正撞见来打太极的老大爷,本想像往常一样低着头走过去,可是脑海中立刻又浮现出那件阳光做的披肩了。
“大爷,早啊。”我从大爷的眼睛里看到了我的笑容,很暖,就像那件披肩。
 收藏
收藏  打赏
打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