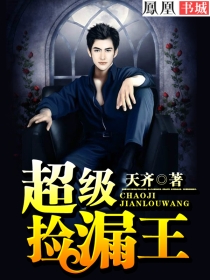正文:粉红的确良(九)
九
二妮家我常去,二妮也常到知青点找我玩。我们手拉着手,走在弥漫着一层薄雾的田间小路。远处有狗“汪汪汪”的低吠声,谁家大娘拉长了腔调:“鸭……鸭鸭鸭……”唤禽畜归窝。青蛙、蟋蟀也拉开清亮的嗓子唱起了歌,各种声音交织成和谐的田园交响曲。半轮月亮升起来了,远处是大片大片的水田,氤氲着一层淡淡的水气,象雾,又象纱,一丝丝一缕缕,起起伏伏。水田映着初升的月亮,闪烁着静谧的柔光。我们俩抄近路,穿过两片水田,田梗上有许多青蛙被我们的脚步声惊得“噗它噗它”跳到水里。
又走过一大片棉花地,棉花已有肩膀高了。
我问二妮:
“要是这次相亲成了,你是不是很快就要嫁走了?”
“不会。还要过礼,走四时八节,最快也得一年以后。”
“还有那么多规矩?”
农村的节日多,平时我们常看见未婚青年走节气,二妮当然也是要走的,但我还是问了一句。
“是要走,我姐姐就是嫁得急了,日子一直过不好,受穷受苦又受气。我爸说,出嫁不能太急了,至少也得把一年的节气走完。再说,爸妈养咱一场,不给家里多挣几年工分就走了,日后要是顾不了娘家,象我姐姐那样,不是更对不起娘家了?”
我们正边说边走,快到家门口时,一个黑影突然从棉花地里窜了出来,把我和二妮吓了一大跳。
原来是赵小伙。只听他压低了声音说:
“二妮子,你不能嫁给那个男人,他有病。”
我和二妮站稳喘了两口气,二妮气得使劲推了赵小伙一把,压低了声音吼道:
“要你多管闲事,死开!”
还骂了一句难听的脏话,然后一把拉住我,紧走几步,到了家门口。
平时舍不得用电,只点煤油灯的二妮家,今天开亮了四十瓦的大灯泡,屋里亮晃晃的,这显然出乎二妮的意料。她用夹在胳肢窝的旧衣服遮盖着膝盖上的补丁。又在门外黑影里掳了掳头发,拉着我一步跨进了门。
八仙桌摆在堂屋中间,上席坐着一个手里夹着烟卷、中年干部模样的人,想必就是田支书了。二妮爸爸正在边客气着“请吃请吃”边向他碗里夹菜。一个红脸堂、胖胖的小伙子正在大口大口地喝酒吃菜,他一定就是二妮未来的男人了。二妮的弟弟陪席。我们一进门,一屋子的目光都聚集过来。二妮的爸爸咳了一声说:
“死到哪儿去了,让人等半天。”
又笑着对我说:
“小董也来了,快上席。”
二妮妹妹三妮忙从灶间跑过来,给我上了一幅碗筷。二妮爸又回头训她:
“死妮子,不快给你姐拿双筷子。”
二妮可能长这么大从没陪生客吃过饭,一头钻进了灶间,死活都不肯上桌。二妮妈和妹妹三妮生拉活扯,才硬把她按在了我和她对象中间。二妮又不肯,非要和我换座位。就这样,我坐在了她和那对象中间。
饭桌上前所未有地丰盛,摆出了当地待客的最高规格:六陆八席,共十二道菜,两大钵汤。菜都用大碗盛着,其中有六个荤菜,猪肉之外还有鸡鸭鱼肉,当地叫水陆空。闻着就让人肠胃“咕咕”叫唤,真不知二妮家用什么方法变出了这么多好菜。
坐稳后,二妮先给田支书夹了一块又肥又大的扣肉,笑着说:
“大伯请吃。”
又给我夹了一块,最后她自己夹了一筷子白菜慢慢地吃。
不一会儿,我就发现二妮这对象有点问题。他不会用筷子,肉和菜都用勺子挖,大口大口地填到嘴里,然后“叭叽叭叽”吃出很大的声响。吃几口,用衣袖擦一下嘴,原来他嘴角总是流涎水。再看那衣袖,崭新的毛蓝制服已经被擦得一片油渍了。
酒菜差不多时,三妮又给每人上了一碗米饭。那对象的肚量真大,一大桌菜被他和二妮弟弟风卷残云般几乎扫光,现在又端着饭往嘴里扒。饭粒顺着口涎撒得衣服、裤子上都是白花花的大米饭。二妮只斜着眼瞄了一眼,便再也不看她对象身上的米粒。
平时吃饭时掉一颗米粒在地上,二妮都要捡起来填到嘴里,今天掉了这么多,二妮一定很心疼,但她就是装做没看见。
饭毕,三妮端上了一盆热水,笑着先让支书洗。支书绞起毛巾略擦了擦脸和手,然后还对着三妮笑了笑,说:“洗好了。”
三妮高高兴兴地又到厨房换过一盆水,端到二妮对象面前说:“哥,您洗。”
这小伙可不象他爸那么斯文,站起来个头挺高,弯下腰把整个脸都伸进了盆里,“噗噗噗”在水里吹了三口气,水花溅了一地。只见他紧闭着眼,接过三妮递到他手里的热毛巾,又放到盆里捞出来,不拧干,顺着一张大圆脸转着圈一抹,胸前便湿了一片,然后把毛巾往盆里一扔。三妮以为他洗好了,刚端起脸盆,他又伸手到盆里捞毛巾,那大手一碰盆沿,三妮没端稳,“哐啷”一声,一盆水扣在了对象的脚上。
对象“唉哟”叫了一声,往后退了两步,我发现他一条腿有点跛。我看了二妮一眼,二妮的脸色暗了暗,很快又笑眯眯的了。
二妮一家人手忙脚乱地给他找鞋换。对象的脚太大,连二妮爸爸的鞋都穿不下。二妮妈忙张罗着让二妮出去借双大鞋,田支书说:“不用了”。这样,二妮对象便光脚趿着二妮爸爸的一双旧鞋,裤腿挽的高高的,傻傻地坐在那里。趁他爸和二妮爸妈说话,不时偷眼看二妮。
这天晚上,二妮家的所有人,特别是二妮的爸妈,都是喜气洋洋的。
二妮家我常去,二妮也常到知青点找我玩。我们手拉着手,走在弥漫着一层薄雾的田间小路。远处有狗“汪汪汪”的低吠声,谁家大娘拉长了腔调:“鸭……鸭鸭鸭……”唤禽畜归窝。青蛙、蟋蟀也拉开清亮的嗓子唱起了歌,各种声音交织成和谐的田园交响曲。半轮月亮升起来了,远处是大片大片的水田,氤氲着一层淡淡的水气,象雾,又象纱,一丝丝一缕缕,起起伏伏。水田映着初升的月亮,闪烁着静谧的柔光。我们俩抄近路,穿过两片水田,田梗上有许多青蛙被我们的脚步声惊得“噗它噗它”跳到水里。
又走过一大片棉花地,棉花已有肩膀高了。
我问二妮:
“要是这次相亲成了,你是不是很快就要嫁走了?”
“不会。还要过礼,走四时八节,最快也得一年以后。”
“还有那么多规矩?”
农村的节日多,平时我们常看见未婚青年走节气,二妮当然也是要走的,但我还是问了一句。
“是要走,我姐姐就是嫁得急了,日子一直过不好,受穷受苦又受气。我爸说,出嫁不能太急了,至少也得把一年的节气走完。再说,爸妈养咱一场,不给家里多挣几年工分就走了,日后要是顾不了娘家,象我姐姐那样,不是更对不起娘家了?”
我们正边说边走,快到家门口时,一个黑影突然从棉花地里窜了出来,把我和二妮吓了一大跳。
原来是赵小伙。只听他压低了声音说:
“二妮子,你不能嫁给那个男人,他有病。”
我和二妮站稳喘了两口气,二妮气得使劲推了赵小伙一把,压低了声音吼道:
“要你多管闲事,死开!”
还骂了一句难听的脏话,然后一把拉住我,紧走几步,到了家门口。
平时舍不得用电,只点煤油灯的二妮家,今天开亮了四十瓦的大灯泡,屋里亮晃晃的,这显然出乎二妮的意料。她用夹在胳肢窝的旧衣服遮盖着膝盖上的补丁。又在门外黑影里掳了掳头发,拉着我一步跨进了门。
八仙桌摆在堂屋中间,上席坐着一个手里夹着烟卷、中年干部模样的人,想必就是田支书了。二妮爸爸正在边客气着“请吃请吃”边向他碗里夹菜。一个红脸堂、胖胖的小伙子正在大口大口地喝酒吃菜,他一定就是二妮未来的男人了。二妮的弟弟陪席。我们一进门,一屋子的目光都聚集过来。二妮的爸爸咳了一声说:
“死到哪儿去了,让人等半天。”
又笑着对我说:
“小董也来了,快上席。”
二妮妹妹三妮忙从灶间跑过来,给我上了一幅碗筷。二妮爸又回头训她:
“死妮子,不快给你姐拿双筷子。”
二妮可能长这么大从没陪生客吃过饭,一头钻进了灶间,死活都不肯上桌。二妮妈和妹妹三妮生拉活扯,才硬把她按在了我和她对象中间。二妮又不肯,非要和我换座位。就这样,我坐在了她和那对象中间。
饭桌上前所未有地丰盛,摆出了当地待客的最高规格:六陆八席,共十二道菜,两大钵汤。菜都用大碗盛着,其中有六个荤菜,猪肉之外还有鸡鸭鱼肉,当地叫水陆空。闻着就让人肠胃“咕咕”叫唤,真不知二妮家用什么方法变出了这么多好菜。
坐稳后,二妮先给田支书夹了一块又肥又大的扣肉,笑着说:
“大伯请吃。”
又给我夹了一块,最后她自己夹了一筷子白菜慢慢地吃。
不一会儿,我就发现二妮这对象有点问题。他不会用筷子,肉和菜都用勺子挖,大口大口地填到嘴里,然后“叭叽叭叽”吃出很大的声响。吃几口,用衣袖擦一下嘴,原来他嘴角总是流涎水。再看那衣袖,崭新的毛蓝制服已经被擦得一片油渍了。
酒菜差不多时,三妮又给每人上了一碗米饭。那对象的肚量真大,一大桌菜被他和二妮弟弟风卷残云般几乎扫光,现在又端着饭往嘴里扒。饭粒顺着口涎撒得衣服、裤子上都是白花花的大米饭。二妮只斜着眼瞄了一眼,便再也不看她对象身上的米粒。
平时吃饭时掉一颗米粒在地上,二妮都要捡起来填到嘴里,今天掉了这么多,二妮一定很心疼,但她就是装做没看见。
饭毕,三妮端上了一盆热水,笑着先让支书洗。支书绞起毛巾略擦了擦脸和手,然后还对着三妮笑了笑,说:“洗好了。”
三妮高高兴兴地又到厨房换过一盆水,端到二妮对象面前说:“哥,您洗。”
这小伙可不象他爸那么斯文,站起来个头挺高,弯下腰把整个脸都伸进了盆里,“噗噗噗”在水里吹了三口气,水花溅了一地。只见他紧闭着眼,接过三妮递到他手里的热毛巾,又放到盆里捞出来,不拧干,顺着一张大圆脸转着圈一抹,胸前便湿了一片,然后把毛巾往盆里一扔。三妮以为他洗好了,刚端起脸盆,他又伸手到盆里捞毛巾,那大手一碰盆沿,三妮没端稳,“哐啷”一声,一盆水扣在了对象的脚上。
对象“唉哟”叫了一声,往后退了两步,我发现他一条腿有点跛。我看了二妮一眼,二妮的脸色暗了暗,很快又笑眯眯的了。
二妮一家人手忙脚乱地给他找鞋换。对象的脚太大,连二妮爸爸的鞋都穿不下。二妮妈忙张罗着让二妮出去借双大鞋,田支书说:“不用了”。这样,二妮对象便光脚趿着二妮爸爸的一双旧鞋,裤腿挽的高高的,傻傻地坐在那里。趁他爸和二妮爸妈说话,不时偷眼看二妮。
这天晚上,二妮家的所有人,特别是二妮的爸妈,都是喜气洋洋的。
 收藏
收藏  打赏
打赏